黄党生/文 网络/图
父亲黄大海的名字,像一粒被风吹落的种子,落在了川北南部县的褶皱里——太霞乡(原罐垭乡)先锋大队黄家坝(现已被淹没),那片被西河流域支流滋养的土地,青山绕着田垄,炊烟缠着竹林,便是父亲生命开始的地方。关于父亲的生辰,没有精确的纸页记载,只凭幺叔黄大清掐着指头推算,大约是1935年的某个清晨,伴着农家茅舍的鸡鸣,他成了黄氏家族六兄弟里排行第五的男丁。
后来我总爱想象,年少的父亲是如何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1950年四川解放前夕,这个农村后生踏上了改变命运的路,关于父亲入仕途的缘由,长辈们的讲述带着几分传奇色彩:一说他跟着剿匪的队伍,踏着晨露穿梭在川北的崇山峻岭,把散落在山间的土匪追得无处遁形;另一说他帮忙背着部队的枪,踩着泥泞走了一百多公里路到南部县府,枪带磨破了父亲的肩头,领队的干部看着他汗流浃背却眼神坚毅,拍着他的肩说“你就留下,给政府做事吧”。父亲从未对我讲过这些过往,那时的我总忙着追逐年少的热闹,竟忘了问一句“爸,你当年怕不怕”。
听说父亲离家前,家里曾为他订过一门亲事。待他数年后揣着思念返乡,却见昔日的姑娘早已成了母亲,怀里抱着几岁的娃娃。他没说一句话,只是望着院坝里嬉戏的孩子,眼底翻涌着说不清的滋味,转身就毅然回了单位——那是我第一次从长辈口中听到父亲的“倔”,后来才懂,那不是赌气,是他骨子里不愿将就的刚。
![图片[1]-纪实散文|我的父亲黄大海-华闻时空](https://ss-mpvolc.meipian.me/users/12626704/origin03ba065f1e640b1138d4fc356d4f0022mpand__jpg.heic~tplv-s1ctq42ewb-s2-cC-q:750:0:0:0:q80.webp)
再后来,父亲遇见了母亲,两颗漂泊的心总算有了归宿。1965年五月,我要降临人世时,却给这个小家出了道难题——母亲分娩我时,我偏偏先把脚伸了出来,在那个医疗条件匮乏的年代,这几乎是把父母逼到了悬崖边。南部县医院的院长和医生围着病床商量许久,最终决定冒险做剖腹产,那是县城里数得着的几例剖腹产手术。医生握着手术刀,再三问父亲“一但出事,保大人还是保小孩?”一生刚毅的父亲竟愣在了原地,双手微微发颤,半天说不出话。当时,父亲不是犹豫,是三十多岁盼子的急切,与对母亲的疼惜在心里翻搅——只是那时的他,还不懂得如何言说这份复杂的爱。如今想来,我敢笃定地说,父亲当时心里一定是坚定地说着“保娃儿”。万幸手术顺利,只是母亲因麻醉药过量,昏迷了七天七夜。父亲守在母亲的病床前,看看襁褓中嗷嗷待哺的我,嘴角抑制不住地往上扬,那股高兴劲儿,真如范进中举般纯粹。后来母亲偶尔拉起衣角,让我看她腹部那道一尺多长的竖形刀口,像一柄生锈的镰刀在岁月里刻下的烙印,每一道褶皱里,都藏着我降生时的惊心动魄。
我的童年,是裹在父亲的臂弯里长大的。虽记不清太多细节,但伏虎片区的长辈们总给我说,当年父亲下乡村工作时,总把你架在你爸肩头“骑马马”。父亲的肩膀宽厚又温暖,像极了黄家坝的小山丘。我趴在他肩上,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和汗臭味,风吹过耳边时,他会故意加快脚步跑起来,吓得我紧紧抱住他的头,他却笑得像个孩子,带着我跑遍了那方的山山水水。父亲有几次带我回老家,我仍然骑在他的脖子上回去,在大坪下车后,还要步行十多里碎石子路,父亲两手腕上还要挂着行李,回到老家,父亲的两只手腕已显紫色了。
十多岁时,父亲去外地开会、出差,总不忘把我带在身边。一次在仪陇县城开什么现场会,中午几十人在食堂吃饭,四方桌挤得满满当当,我仗着年纪小,麻溜地抢占了父亲的座位,上桌就和叔叔们抢着夹菜吃起来。父亲没说什么,只是端着一碗干饭,静静地站在我身后,像一堵坚实的墙。桌上的红烧肉油光锃亮,那是那个年代最诱人的美味,可他始终没动一筷子;若是遇到每人只有一块的扣肉,父亲更是连目光都不往那边落。食堂窗外围了上百人,都眼巴巴地望着桌上的肉菜,而我只顾着狼吞虎咽,全然没有去理会父亲站在我的背后,父亲的目光始终落在我埋头吃饭的背影上。
![图片[2]-纪实散文|我的父亲黄大海-华闻时空](https://ss-mpvolc.meipian.me/users/12626704/origin9645d0b11a7dceb0d33e7b87c055a420mpand__jpg.heic~tplv-s1ctq42ewb-s2-cC-q:750:0:0:0:q80.webp)
小学三年级时,我在老家柱头庙小学读书,突然我闹着要跟父亲去伏虎读书。父亲和母亲面面相觑,半天摸不透我的心思。父亲蹲下来,摸着我的头问“为啥非要去伏虎读书?”我仰着脖子,带着孩子气的赌气说“你天天在外面吃好的,不管我们!”父亲听完愣了愣,随即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那时的我哪里知道,他在外“吃好的”,不过是开会时偶尔能沾上点荤腥,多数时候,他揣着干粮就往乡下跑、靠农家端上一碗酸菜红苕稀饭充饥。可第二天,父亲还是收拾了我的书包,牵着我的手往伏虎走,在我眼里,那便是当时最繁华的“大城市”——伏虎。
到伏虎读书后,我竟动了偷父亲的钱的念头。父亲的卧室里摆着一张三抽屉办公桌,左右抽屉上锁后会留一道细缝,里面放着父亲每月五十四块五的工资。我天天蹲在桌前研究,终于想出了办法:找一根细铁丝,一头磨得尖尖的锋利,一只手举着手电筒往里照,另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把铁丝伸进去,对准钱的边角轻轻一戳,就能稳稳拖出两块钱。每次偷完我都心惊胆战,却又忍不住隔些日子又来一次。
纸终究包不住火,父亲还是发现了钱少了,只是他没戳穿我,只轻声问“你拿我钱了?”我梗着脖子喊“没有!”他便没再继续追问,依旧把工资放在原来的地方。后来的岁月里,我无数次想开口问他“爸,你知道我偷你钱了,你还是把钱放在那里?”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那几十块钱在当时是全家的生计,我偷走的十几块钱,够买好多天的全家口粮。而我拿着偷来的钱,带着同学去饭馆买三毛钱一份的回锅肉,有时还三五份,看着他们围着我欢呼,竟觉得自己很威风——如今想起,那威风的背后,是父亲沉默的包容,是他宁愿自己省吃俭用,也不愿让我难堪的爱。
![图片[3]-纪实散文|我的父亲黄大海-华闻时空](https://ss-mpvolc.meipian.me/users/12626704/origin2047b89a293c4f6934a9185e264dfef0mpand__jpg.heic~tplv-s1ctq42ewb-s2-cC-q:750:0:0:0:q80.webp)
七十年代末,升钟水库要修建,我们家在淹没区内,全家人便跟着父亲搬到伏虎安家。父亲做了一件在当时惊动了省领导的事:他在镇上买了一小块地,要建一座小四合院,主房还是三层楼长四间。那时伏虎的两层楼都少见,我总好奇他从哪儿弄来的材料和钱。后来才知道,建房的木料是老家旧房拆下来的,砖瓦、水泥、石头有不少是朋友相赠,最让人动容的是用工——伏虎片区的乡亲们自发赶来帮忙,没人要一分钱,还自带上干粮当午饭。张家大爷天不亮就扛着锯子来锯木头,李家婶子背着竹篓装着自家蒸的红薯,王家叔伯带着锄头来平整地基。他们说“黄书记帮我们修过水渠,帮娃们办过学校,还帮我家娃解决了生病就医问题,出这点力气算啥!”乡亲们排着队来干活,院子里炊烟袅袅,人声鼎沸,那场景,如今想来仍像一场温暖的梦。
搬家伏虎后,家里开支陡增,我和两个弟弟、幺妹都在上学,母亲每天清晨就起来煮红苕稀饭或苞谷稀饭,偶尔炒一盘花生米,都要小心翼翼地分到每个人的碗里——若是让我和大弟自己挑,小弟小妹恐怕连一粒都吃不上。父亲工资低,可我们总馋肉,父亲便想了个办法:去食品站买猪头回来,能凉拌、能红烧、能炒能蒸、还能炖汤。每次炖猪头时,院子里都飘着香味,我们姊妹四个围着灶台转,父亲坐在一旁抽烟,看着我们馋猫似的样子,眼里满是笑意。只是苦了母亲,她要坐在煤油灯底下,用镊子一根一根拔猪毛,指尖被扎得通红,灯的光把母亲的影子拉得很长,那股猪毛的腥气,她一忍就是大半宿,直到现在,母亲提起这事还忍不住摇头。
![图片[4]-纪实散文|我的父亲黄大海-华闻时空](https://ss-mpvolc.meipian.me/users/12626704/origin7a5095fa10020d8ed106143ba9a17d7dmpand__jpg.heic~tplv-s1ctq42ewb-s2-cC-q:750:0:0:0:q80.webp)
房子修好后,我们最怕吃饭时有人来找父亲——来的大多是遇到难处的乡亲,有的衣衫褴褛,有的面带愁容。父亲只要听见敲门声,放下碗筷就去开门,第一句话准是“吃饭没?”若是对方说没吃,他立马把人往桌边拉,把自己的碗推过去“快吃,我不饿”。我们没少埋怨父亲,可他总说“人家来找我,肯定是有事过不下去了”。还有单位打牙祭时,父亲总匆匆吃几口,就盛上一大碗肉,假装边吃边往家里赶,脚步快得像怕被人看见。一进家门,父亲就把我们叫到跟前,用勺子把肉分到每个碗里,眼神里满是宠溺,像老鸟把最肥美的虫子喂给雏鸟——那碗肉的香,我记了一辈子。
父亲的文化不高,可能只读过几年私塾,可他总说“人要活到老学到老”。每晚饭后,父亲就坐在桌前,看书看报,练习写钢笔字,写的不好就翻过纸张在背面又重写。后来他还去党校多次学习,慢慢竟能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父亲还试着给《南充日报》、《四川日报》投稿。那些稿件,他改了又改,有时写到深夜,电灯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一幅安静的画。没想到,他的稿子真的被采用了,后来还和《南充日报》的编辑成了好朋友。
受他影响,我读初中时也开始投稿,竟也屡投屡中。一次我写了篇题为《在生不孝死了干闹》的杂文,发表在《南充日报》上,占了两个豆腐块大小的篇幅。父亲看到报纸时,高兴得像个孩子,拿着报纸四处炫耀,见人就说“这是我大儿子写的!”父亲把那篇杂文剪下来,压在办公桌的玻璃底下,放在正中间的位置,直到退休时才取下来。后来父亲把我发表的文章都剪下来(只是他看见我发表的文章),装订成一本册子送给我,可那时的我年少轻狂,觉得这些“豆腐块”算不了什么,随手就放忘了地方。如今想来,那本册子里藏着的,是父亲最朴素的骄傲。
![图片[5]-纪实散文|我的父亲黄大海-华闻时空](https://ss-mpvolc.meipian.me/users/12626704/origin545dfb88741363d6314ed00de67d8f7ampand__jpg.heic~tplv-s1ctq42ewb-s2-cC-q:750:0:0:0:q80.webp)
父亲对黄氏家族的后生,总想着能帮一把是一把。堂哥想去学医,他骑着自行车跑了几十里路,找老医生求情;堂哥想当老师,他把自己珍藏的书本送过去,鼓励他首先要努力学习;堂姐想跟着他读书,父亲就把堂姐带到身边上学,每天督促她写好作业。尽管这些后生没有出类拔萃的,可父亲总说“只要他们能好好过日子,我就放心了”,偶尔还会自责“要是我本事再大些,就能让他们走得更顺些、更远些”。
退休后,父亲总惦记着黄家坝的黄氏家族亲人,时常买些食物如白砂糖、务农物资如尿素之类的东西送回去,每家都送。有一次,父亲把物资交给货车司机捎走,自己却拦了辆摩托车返乡。川北的山路颠簸不平,他紧紧抓着车座,回来时腰就闪了,在床上躺了几个月。我们埋怨他“这么大年纪了还折腾”,他却笑着说“看见兄弟们、侄儿侄女好好的,我就踏实了”。
父亲当了一辈子小公务员,心里装的全是百姓。他总说“当干部要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可这份“良心”,却让他错过了好几次提拔和涨工资的机会——他从不肯说假话,每次向上级汇报工作,都把百姓的疾苦如实说出,哪怕会得罪人。有人劝他“少说几句,对你有好处”,他却梗着脖子“百姓的苦不能瞒,我问心无愧”。他还常念叨“运动太多,百姓遭罪”,可又无力改变,只能叹着气说“我这是搬起石头砸天”。按政策规定,1949年前参加工作的人员能办离休,可父亲的档案丢了,最后只办了退休。他拿着退休证,摸了摸封面说“没事,能安安稳稳过日子就行”。
![图片[6]-纪实散文|我的父亲黄大海-华闻时空](https://ss-mpvolc.meipian.me/users/12626704/originc6d256780ce06abc0ee42ea1058908bbmpand__jpg.heic~tplv-s1ctq42ewb-s2-cC-q:750:0:0:0:q80.webp)
可父亲终究没能安稳太久。他去世前两年的一个下午,华西医院的医生把我们几个叫到办公室,轻声说“你们父亲得了食道癌和贲门癌,晚期了”。后来陈德静老爷子亲自去华西,请了多位专家会诊,结果还是“手术意义不大,回家康养”。我和弟弟送父亲回南部时,在车站道别,我突然发现父亲老了——头发白了大半,背也驼了,眼神浑浊得像蒙了一层雾。我握着他的手,那双手曾经扛过枪、救过他人、写过稿、抱过我,如今枯瘦如柴,布满皱纹。那一刻,我才猛然惊醒:我还没来得及为父亲洗一次脚,还没来得及陪他喝一次酒,还没来得及说一句“爸爸,您辛苦了”,他就要走了。
后来我才悟到,父亲那时可能同时患有抑郁症。黄氏家族给他的压力,我们给他的压力、经济上给他的压力……他总是坐他床边的藤椅上发呆,眼神落在远方,夜里睡不着时,就念叨着“老大经济状况差,家庭也不顺利;老二的工作顺利不,一段时间没来电话;老三又到那里出差了;幺女还小,说还要生一胎……”父亲放心不下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我——这个被他娇生惯养长大的大儿子,没履行好长兄如父的责任,个性又刚烈,成了父亲最大的牵挂。
![图片[7]-纪实散文|我的父亲黄大海-华闻时空](https://ss-mpvolc.meipian.me/users/12626704/origina774cf412ae81f4579979bbbb6fadf73mpand__jpg.heic~tplv-s1ctq42ewb-s2-cC-q:750:0:0:0:q80.webp)
父亲走后的第二年春天,我突发脑溢血,在华西医院抢救了六七天,才算捡回一条命。昏迷期间,我反复做着同一个梦:梦里是广元市那边的山貌,半山坡上有一扇黑漆漆的门,门里阴森无比,很多人抢着往里跑,我也跟着挤了进去。可刚进门,就清晰看见父亲站在门里面,眉头皱得紧紧的、惊恐万状,父亲朝我吼道“混账东西,你来这里干啥!”声音里满是焦急。我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慢慢退了出来,醒来时枕头全湿了。
出院后,我总觉得父亲还在身边。每次坐在我常坐的椅子上,都觉得旁边有他的气息;吃饭时,总觉得他站在我身后;睡觉时,总觉得他坐在不远处看着我,像当年看我写作业的情形。我把这些事讲给我的亲朋好友听,他们都说“是你想父亲想多了,是幻觉”。可我知道,那一定不是幻觉——人的肉体或许会消失,但灵魂不会,父亲一直在我身边,从未离开。
![图片[8]-纪实散文|我的父亲黄大海-华闻时空](https://ss-mpvolc.meipian.me/users/12626704/originc81e0195101a2d2ddef03b00257f56f0mpand__jpg.heic~tplv-s1ctq42ewb-s2-cC-q:750:0:0:0:q80.webp)
五十岁以前,我总嫌父亲固执、不懂变通,觉得他这辈子没混出啥名堂;可当我历经大半生风雨,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才明白父亲站在百姓面前的挺直脊梁,藏在沉默里的包容,面对困境时的淡然,都是我一辈子学不来的本事。我不但没做好儿子,也没做好父亲,没把父亲教我的善良和责任传承下去。
如今我一个人独处时,总爱回忆我和父亲的点滴故事,既安然处之、又心如刀绞……我忍不住跪了下来,泪水砸在地上,嘴里喃喃道:“爸爸,要是有来生,您来做我的儿子吧!我会把您架在我的肩上,带您走遍您没去过的地方;我会给您点最好的饭菜,请您的好朋友都来和您共享盛宴,不让您再站在我身后吃饭;我会把我的文稿好好珍藏,像您当年珍藏我的文章那样。爸爸,来生您来给我当儿子吧,我一定好好宠您,把您给我们的爱,一点一滴都加倍还给您……”
【作者简介:黄党生,自由撰稿人,曾历任多家报刊、大型网站、记者、编辑、主编、总编等;现担任多家网络平台主编(主播)。】
![图片[9]-纪实散文|我的父亲黄大海-华闻时空](https://ss-mpvolc.meipian.me/users/12626704/origincad8f8f128ab21c01264010b6aabafc0mpand__jpg.heic~tplv-s1ctq42ewb-s2-cC-q:750:0:0:0:q80.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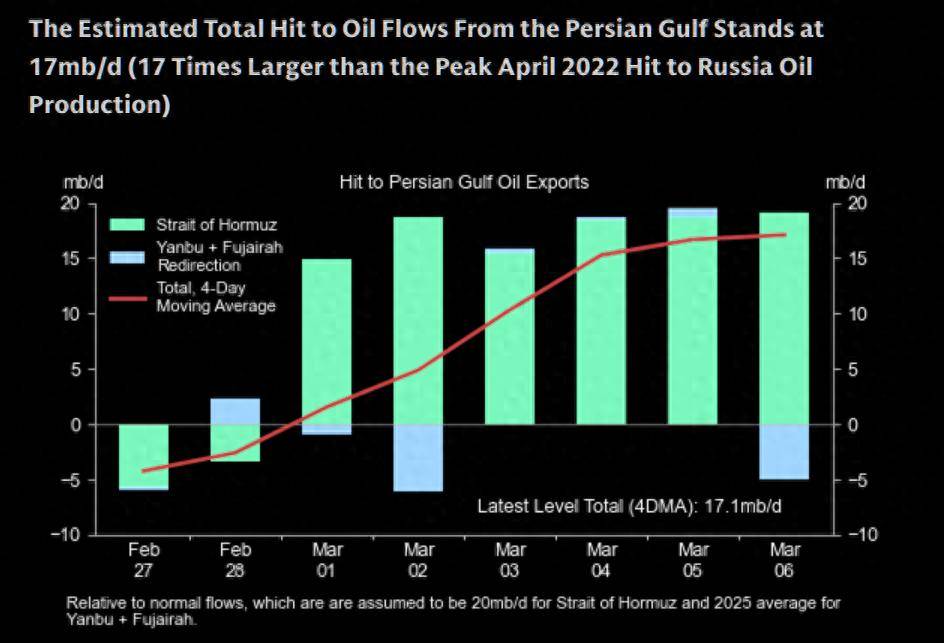






- 最新
- 最热
只看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