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山公众号新开一个专栏:《文学偏见》,作者黄惟群。
黄惟群拥有知青背景,上海籍,赴澳洲三十多年,自学成才,出版和发表文学作品无数,遍及大陆,台湾,香港,美国。我们看中他的一本文学评论《偏见集》,专门针对文学潮流,尤其针对家喻户晓的名家和名作,发表不同意见,实在难能可贵。
这些不同的看法与其说是针对作者的,不如说是给读者听的;与其说是告诉读者的,更不如说是棒敲文学评论家的,因为在字里行间他们引领读者亦包括作者,带着无冕的皇冠,发出权威的声音。
挑战权威谈何容易?作者先给自己戴一顶“偏见”的帽子,留给权威们足够的面子,同时为自己掘开一条缝隙,谨慎地传递关于文学的肺腑之言。这声音传了七八年才传到美国。
而此时,黄惟群已经退休搁笔,但并不妨碍他的声音传播。
经他同意,开此专栏,以飨读者, 求共鸣或争鸣。
引言
将理论当眼睛在作品寻找印证物,用学过的理论去套作品。一些看似自娱自乐的文学评论,不仅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并且确实影响控制着文坛。
文学评论写给谁看?无疑,写给读者、作家看。然而,太多中国文学评论,不说读者看不懂、没兴趣看,就连作家也看不懂、也没兴趣看乃至讨厌看。可以说,中国文学评论文章中的大多数,除了评论家自己,没人有兴趣。这话很难听,却是个谁都看见的不争事实。然而,正是这样一些看似自娱自乐的文学评论,不仅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并且确实影响控制着文坛。一个有趣现象:即使看不起甚至讨厌评论家的作家们,却还关心着评论家左右的文坛动向,关心着自己在这动向中的位置;一个更有趣的现象:一些骄傲的作家一旦碰到评论家所表现出的热情、欢喜与尊敬,判若两人的程度让人目瞪口呆。浅里说,作家们希望评论家将目光转向自己,深里说,恐怕牵涉到国民性。
既矛盾,又统一,是矛盾的统一。正是这样矛盾的统一,成全了中国文坛现状。
我们的文学评论究竟是些怎样的评论?客观地说,大多是些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评论与被评论间很少发生实质关系的空乏之说。生涩、华丽、崎岖、诡异、巨室少珍、理拙文泽、纸上谈兵、夸夸其谈,让人不知所云、如鲠在喉,无法下咽,却同时,又让人感觉经典沉深、载籍浩瀚、不敢等闲视之。
一些从学校到学校的评论家们博学强记,让人佩服,但他们学有余而识不够;他们阅读作品,是将理论当眼睛在作品寻找印证物,用学过的理论去套作品的。当然,这里说的只是“一些”。
无论如何,当今中国文学评论太多理论,太多脱离实际、与文学作品中的大历史如出一辙的貌似强大的理论,太多鹦鹉学舌、别人理论的重复,太多理论原创者如果健在多半会想修改的理论。
理论来自作品,而非作品来自理论。理论是实践的总结,恰恰又只有放回实践中有效运用,才具价值。于评论家,理论是家底、素养,基本功,是资本的积累,是赖以仰靠的大山。
评论家的每次征程,都该在这样的仰靠下出发,将化为大山之石的理论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地用以分析作品。理论与评论的关系,如同身体与营养,有个吸收、消化、再生的过程。和任何知识一样,理论知识越多越好。但是,并非知道的就是掌握的。理论本身有对错之分、有理无理之分外,还有合不合你、能不能被你消化、被你取为己用的重大问题。只有被你消化的理论才是你的,那些消化不掉的,即使再高深,也与你无关,就算借你,你也用不好。至于那些已被吸纳融化进你思想认识体系的理论,也不是被你用来照搬的。理有恒存,思无定契。理论是被掌握它的人拿来活学活用的。作为文学评论家,重要的是将已被掌握的理论,化繁为简,以简制繁,深入浅出,举重若轻,乘一总万地予以运用,能够的话,再展示一定语言艺术的形象性与生动性,让理论不像理论。
一个在写评论时还惦记着学过理论的评论家,绝对是个死板、愚笨、木纳、缺少见地的批评家;一个需要发表独立见解时还惦记着别人说了什么、怎么说的,还企望在别人的见解中获取自信、靠别人的见解支撑自己的评论家,绝对是个不够格的评论家。
被中国文坛激情万丈地敬仰崇拜得足以头昏的夏志清教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他写文章时是从来不想理论的。这才是自负、骄傲、艺高胆大、头脑清醒的人说的话,才是值得大家认真一听、认真一想的寓有真理的话。
沈从文写《论郭沫若》,其中没说一句别人说过的,没说一句生涩费解貌似深奥的,但读完文,你会觉得,这人太厉害,看人看事看文是越骨头里看的,是看透了本质的,你会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评论”。
重复别人说过的话,不仅无聊,而且无才。
有一点很肯定,文学评论中,一个满纸理论的人,一定是个还没搞懂理论的人。
事实上,当今的中国文学评论中,蜂拥而出的理论已成为一种作者的炫耀手段。我们的评论家中的不少,乐此不疲地忙于开列清单,展示自己读书之多、之广、之偏,并将开出的清单作为自己实力的证明。
一位著名评论家授人写作之技时曾经这么说:“要多用名家的话,越多越好,越冷僻越好,越难懂越好。”――一个老实人,一个老实的滑头人。很多人这样做,但都只做不说,他是又做又说,还要授人。
可悲的是,这样廉价的诡计确实可行,确实吓倒许多人,并让许多被吓倒的人对之抬起仰望的头。
“这篇文章写得好。” “好在哪?” “没看懂。” “没看懂为什么说好?” “就因看不懂,才感觉它好。”
一段真实、生动的对话。一段很说明问题的对话。
有作家说,如今的文学评论不过是些“中心思想”。确实,不少评论说的都是作品反映了什么、说明了什么、表达了什么,诸如曾被广泛当作真理传诵的“表达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之类。
这是否也与“统治”文坛的“大”之理念有关?大理论、大评论、大历史、大政治、大文学。彻底地抛弃一切的小。这让人不得不怀疑,是否胸中无大之人才会格外爱大?几乎已没文本分析、已没作品论。没人再有兴趣谈谈具体作品好在哪不好在哪,谈谈哪个细节起了怎样的作用,哪个形象是靠怎样的细节勾勒出的,谈谈文字技巧的魅力,谈谈哪段文字制造了怎样的感觉、达到了怎样的效果,谈谈已达的效果与局部、整体的关系、以及与作者希望达到的效果是否合拍、其间存不存在差距......太多太多。太多作家想听、读者想听的赏析,太多能给作家、读者带来触动与帮助的提醒,太多文学评论家真正该做须做的责无旁贷的事。
至于中心思想,不是不需要,而是不能光有。就算小学语文,中心思想前,还得课文分析,还需讲解结构、层次、段落大意,还得做些文字推敲、语言玩味、细节讲解。缺少了这些步骤,凭空获得的中心思想,就算再伟大,也是空中楼阁,没有到达的梯子,有没有实在关系不大,或许没有更好。没有了这样的空中楼阁,至少抽去一块可以信口开河的平台,不至增添不必要的扰乱。
一个优秀评论家,首先应是一个优秀读者。作为优秀读者,必须具备的是良好的理解能力和良好的感悟能力,阅读作品时,应首先打开的是自己的所有感官,充分并且正确地接受作品中发出的任何一个信号。这样前提下,才对阅读中得到的感觉与自身储存的感觉进行碰撞,进行比较分析辨别。读者的认识起于感觉,是以感觉为基础的。人的感觉是最“原始”、最直接、最根本的对事物的反应,是个人思想情感的综合;再高的理论,也离不开最基本的感觉。
一个优秀评论家,在首先是个优秀读者的前提下,如能了解并且懂得创作、懂得作家的话,他的评论将可能更全面、更准确、更可信、也更精彩。根本来说,作品是作家全控制的产物。作品中,大局小局框架细节甚至语言运用,说到底,都是作家的精心设计,是作家有预谋的操纵。只有作家自己最清楚自己的用心,知道自己想达什么效果,怎么具体制造这效果。也因此,评论家评论的作品用心不是作家用心的话,那么,说得太漂亮也不足以信;不说有害,不说误导,起码可说,其存在的价值几近于零。毕竟,评论的准确性不能完全寄托在作家们的歪打正着上。
不要再说理论了。当今中国文坛真正需要的,不是仅和理论对话仅和评论家對話的所谓理论,而是既和作品對話又和作者對話的作品論,特别是今天。理论是灰色的、枯燥的。能对中国文坛起到真正作用的是具体文本分析。也只有具体的文本分析,才能帮助作家看清自己,帮助读者看清作品,我们的评论家也才能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理论究竟掌握如何、有用无用。
作者简介
黄惟群
出生: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国籍:澳大利亚
作家,评论家。一九八六年始发表作品,在中、港、台一百多家杂志报纸发表小说、散文、随笔、评论二百余万字。大量作品被国内杂志报纸转载,文学评论及散文屡被收入国内权威选集。
1987年移民澳洲,曾任当地华文报社记者、总编辑。1994年获“澳洲第一届华文杰出青年作家奖小说奖”。1995年由《香港明窗出版社》出版小说散文集《不同的世界》。1996年《不同的世界》获台湾华侨联合总会“小说佳作奖”。2002年由日本《光生馆》出版社出版黄惟群个人专著中文教科书《澳洲风》。2005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黄惟群作品自选集》。2016年由《天涯》出版社出版个人文学评论选《偏见集》。
在《上海文学》《花城》《小说界》《作家》《清明》 《广州文艺》等杂志以及《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羊城晚报》《新民晚报》《中国青年报》《文学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北京日报》等中国大陆报纸发表作品。亦在海外的《中央日报》 《中华日报》 《明报月刊》《香港文学》 《大公报》《星岛日报》《世界日报》等媒体发表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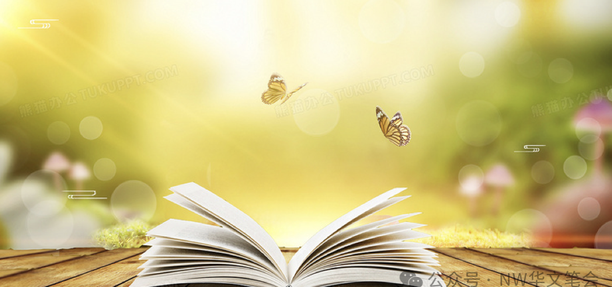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