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至1975年,新三届的知青先后纷纷下了乡,而他们中有人在农村刚满两年就因父母关系到位很快回了城,相反1966、67、68老三届的知青还有少部分人坚守着农村,不用说我当然是其中一员。我现在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农民了。
1975年,上面的政策似乎有了变化,农民可以随意上街买卖农产品而不再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社员们大量喂起了鸡鸭,自留地搞得更是火热,而队上的农活,只要过得去,出工不出力的现象越发严重了。但这时的我已经知道,这不能怪农民自私,社员谁不会算经济账,事关衣食住行切身经济利益,经济没基础,何来意识形态的高尚呢?
我已经学会了一年四季的农活。我收集了农民种庄稼的谚语,诸如“立夏苕,最大条”,“芒种忙忙栽,夏至谷怀胎”“麦出火山谷掉泪”等等,六年多的知青生活,让我晓得了什么时间种什么粮食,什么时间庄稼收割入仓。我完全掌握了农业生产,而且许多方面我还比农民强哩!
比如自留地种瓜,打窝子下底粪,大家都这么干的,可我种的南瓜、冬瓜、丝瓜,都较社员种的瓜结得多,瓜更大。农民们诧异了,溜到自留地来看,我告诉他们说,这不奇怪的,你们一窝里只留下两株瓜秧,多余的都拔出来撂了,我却留下四株瓜秧,剪掉其中两株的头,分别嫁接到另两株上去,这样就比你们的瓜藤长得又快又壮,到藤蔓开花,再打掉旁枝、空花,自然结的瓜就多了。这些科学种庄稼的事书上有介绍,加之自己多动点脑筋,就行了。农民说,难怪是知识青年,到底读过些书的人,就是不一样。
于此我有了些在农村生存的资本。虽眼看着周围几个公社老知青只剩下王五和我,新下乡的知青又有不少也回了城,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已习惯了农村独自一人的生活,并且能在乡下发话有人听,不免又得意了几分。人啊,就是皮子贱!可就在我自以为是时,却不料在一次帮工为农民修房的重体力劳动中,队长张成中的一席话,醍醐灌顶,方使我真正成人。
偏远山区的农村习俗,青年18岁就谈婚论嫁,20岁就结婚生子,之前家里大人要修房立屋,这是农村中最最重要的大事。农民年年省吃俭用,为的就是这修房立屋,完成儿子打发女。
1975年冬季农闲,天不亮帮工的人就起床到了被帮工人户的家。农村建房子,采用的都是这种互相帮工不计报酬的方式,即不讲工钱,只管吃饭。大家聚拢,主妇先打来一盆热水叫洗脸,一张帕子洗十几个人的脸,因全队都是一个姓,有干部头衔的,辈分高的就先洗,到后头,一盆水竟成了黑浆子,但农民说“污水不污人”,照洗不误。接着是吃早茶,其实就是一大碗面条,吃完用手把嘴一抹,带上绳索木扛便往石窠处去。石窠在对河岩,将条石抬出来要经过好几沟田坎,没有相当的体力是抬不动的。千多斤重的条石,八个人在田坎上挪步,当转弯处磨角时,处在尾后的人肩上杠子尤其沉重,腰沉得散了架似的却也得咬紧牙关挺过去,这滋味,不是过来人,真不知其中的苦。
从天麻麻亮抬到中午,快到吃饭的时间,那最后一趟我真是抬不动了,腰真散了架,支不起,眼看就要窟下去。成中看我咬牙硬拼,额头大汗,便叫声大伙歇了气。抽口烟,再抬,成中把绳子往他那头挪了挪,我这头轻了些,这才将石头抬到晒坝旁的一块空地上,新房基就坐落在那里。然后到老湾头大院吃午饭,是白米干饭兼几片隔年的老腊肉。农民们一年四季,只得这帮工的时候,才有此饭吃。
吃罢饭,我从大院出来拐弯步上晒坝,在自家门坎上坐了看天。冬阳几分暖和,白云悠然飘移。山坡上,这些年柏树长高了不少,虽为烧柴农民砍过了坡,青杠、荆棘只留下了第二年生长的根桩,为了给猪牛布窝连草皮也铲了,但山上还是有了好些绿意。山下的坡地,点的麦子苗刚抽头,浅浅的翠色,大地像刚铺了绒毯。坡下的水田,闪着亮光,波纹细细的;偶或看得清一两只白鹭,盘旋而来,飞立田中寻食。农村是有诗情画意的,但那多属于有闲的文化人,而农民,千百年来不识字,况且他们也没有空闲时间去吟什么“草盛豆苗稀”啊!
“老邵啊,你下乡六年了吧。”成中不知何时已坐在身边,待他说了话我才发现他正看着发呆的我。
“唉,是,六年多近七年了。”很小的应声,那可是从心底流出来的话。
“嗯,你一个人过日子真的不容易呀!你也不小了,像农村中的人,娃儿都该有两三个了。农民嘛,就该现实点,农民就最讲实际。你就拿这些木匠、石匠来说,”他指了指晒坝旁正在宅基地下基脚的匠人,继续道,“他们有手艺,钱来得泡活些,人们对他们也尊重些。可他们也有难的时候。木匠怕打望天眼,石匠怕打扒海眼。在山上打石头,十斤重的大锤,弄不好要命的。刨生活嘛,总是要吃苦的,活人哪,谁个不艰难?有饭吃,有衣穿,就不错了。还造个啥子反哩。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百姓都是命注定,你就不要再去写那些东西,动些歪脑筋干啥子!还是考虑考虑怎么过日子,在农村安个家才是正经的。”
我脑子恰似五雷轰顶,我真没想到这一步,竟然要在农村、在僻远的丘岭山区过一辈子,我真不知该如何回答是好。
队长张成中是队上唯一读过几天中学的人,他父亲是大队书记的堂哥,队上就他文化高些,明白事理些。他年龄不过三十出头,大我不了多少,但他已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了。
成中看我没说话,便又道:“也是,也是,农村吃没啥吃的,穿没啥穿的,农活又繁重,苦得很。你们城里人终归是城里人,迟早要回城头去的。千年的百姓流水的官,朝廷总是要变的。等等看吧,也好,如实在不得变,也要现实点才好。”
农民的智慧啊,既现实而又机敏,让我无言回答。我还自以为自己看过几本书,就高明于别人了,其实不然。书本知识如不与实际相结合,书便是白读了。而一旦将书中的知识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那我们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就会有质的飞跃,如此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待帮工结束,吃了晚饭回到家,我坐在煤油灯下开始对自己二十五年来的岁月认真思考。我决心重振生活,抛却曾因乱写东西而带来的阴影。我决定白天在队上劳动,晚上看书,重新拿起好几年不曾动过的书,开始想这社会、这人生,究竟应该怎样过。
作者简介
邵培德,1969年重庆下乡南部县知青,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2010年四川省南部中学退休,2020年在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高开教坛。全国模范教师,特级教师,曾任四川省中小学高级教师评委。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个人专著《培德文集》,撰写高中选修教材《国学概览》等多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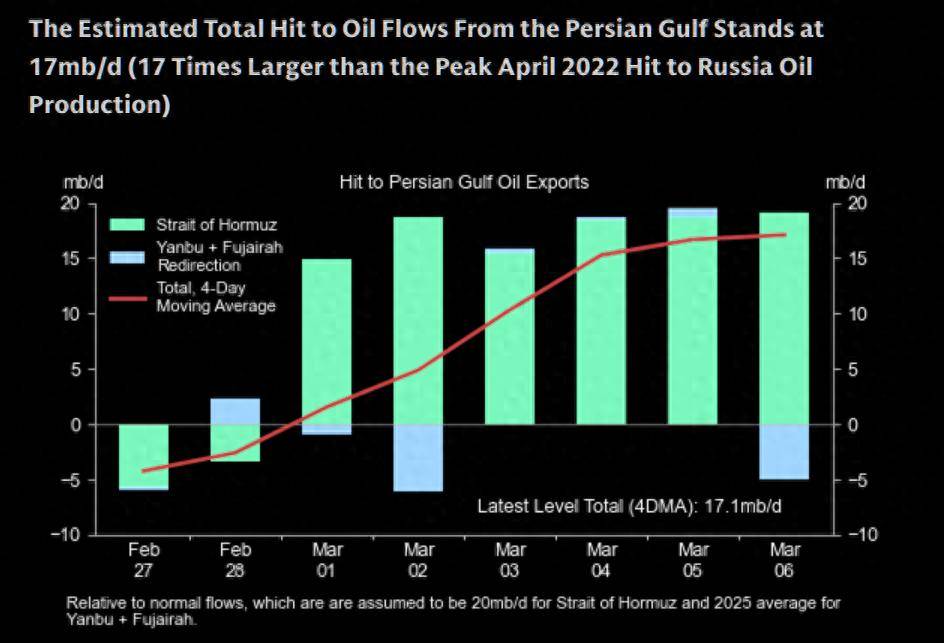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