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许多次,我都试图进入这样的一个历史场景——昏暗的灯光下,一位身着土布青衫的老者正在一纸信笺上悬腕写着,但他又忽而停笔凝思、沉吟片刻,羊毫笔锋沾了沾墨,接着便一挥而就:
“人常患不知读书,知读书矣,犹患其不能立志,能立志矣,仍患其误于所志,而辨之不早辨也……”
这是余潜士写给他侄儿余习昌、门生王时开的信。彼时,这两个懵懂少年正在家乡永泰蓝田观就学。“蓝田山不高,仙观傍其下。地以仙得名,清溪绕绿野。”蓝田乃永泰县同安乡(旧称辅弼)之“胜概”,蓝田观“处廖寂幽僻之境”,正可静心向学。
余潜士是很喜欢侄儿余习昌、门生王时开的,他31岁的那年夏天,还带着王时开等一众毛头小孩出游辅弼岭。
![图片[1]-徐德金||塾师余潜士:遥遥俯仰天地间,一介寒士种春田-华闻时空](https://hwsk.oss-cn-shanghai.aliyuncs.com/2025/09/image-74.png?x-oss-process=image/auto-orient,1/quality,q_90/format,webp)
【余潜士(1784~1851),字时缵,号耕邨,永福县人(今永泰县同安镇樟坂村龙墘厝)。清代福建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少年希志圣贤,因偶读《近思录》,遂有志钻研宋五子之学。只身往高盖山读书,潜心研读宋儒著作,对朱熹《小学》尤有研究。嘉庆十二年(1807),总督汪志伊欣赏余潜士的才学,令其入鳌峰书院教学,帮助辑注《小学》。道光二十三年(1843)中癸卯科举人。咸丰元年(1851)去世,敕授文林郎。咸丰四年(1854),入祀乡贤祠并配祀孔庙,享春秋官祭。著有《耕邨全集》十五卷、《礼记揭要》、《举业汲绠》等。遗著在咸丰间由其儿媳张瑞贞整理汇编成《耕邨全集》刊印行世。】
回想自己年二十,“乃独往高盖山寺,蹑石磴一千余级而上,发愤自读者四年,志向颇坚……俯仰宇宙,不复知人间更有可乐之事。”用一封信,余潜士将自己读书心得倾囊相授。
这是一封长逾千字的“劝学”信,在《余潜士全集.姑留稿卷》中,这样篇幅的文字并不多见。
这封千字信,余潜士花了多长时间?今天,我就站在福州南后街宫巷的入口处,回望180年前那位为家乡子弟漏夜秉笔的长者,不知道他一生中写过多少封这样的信札。
作为一名私塾先生,从28岁开始授徒塾馆,至68岁去世,前后凡40年光景。据记载,余潜士先是在福州鳌峰坊高氏馆,课其子侄,凡十载;期间在侯官穆江大穆埕陈氏馆授徒课读半年;41岁“馆于本县江氏课徒”;又,其戚党黄栋轩“延予于家塾,授经七载”。60岁始,馆于郡中东门外魏杰之寿泉精舍,直至68岁返永泰故里。
我们现在很难还原余潜士课馆的情形;但我们从他留下的一些文字,多少能够了解他“授业解惑”的旨趣。
在余潜士成为私塾先生之前,他是永泰偏远乡村辅弼乡的农家子弟,父亲早逝,靠二伯父“奔走服贾”卖药以供给读书,在乡间塾馆辗转数年,“自嘉庆庚申年,时年十七,承伯父命,始出门就傅,榕城三载,行踪不越郡邑间”。不过,他外出从师,“就傅不知励学”、“多荒于嬉”;由是,后来也颇多自责。他说“予年二十,始知自奋。”
从二十岁开始,余潜士在高盖山苦读四年,心智大开。“因阅《朱子文集》《语类》,论及道家神仙之学,有《参同》《悟真》诸书,遂窃喜搜求而渔猎之。”余潜士尤其对《小学》进行深入研读,并感赋七律二首,认为“小学篇篇细指迷,六经四子此阶梯”,成为为其后来私塾授课蒙童的最好“教材”。
二、
余潜士“数十年濡首载籍,与古为缘”,“复奔走于笔耕,沉浮于科举,泛滥于杂家”,终成饱学之士,被誉为“吾闽道学之宗”、“理学之东南重镇”。
余潜士的理学成就自有公论,而我则从他“为稻粱谋”的课馆生涯,翻开他经世致学的璀璨一页。韩愈在《师说》一文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韩愈因李氏子蟠“学于余”而作《师说》以“贻之”。上文余潜士给他侄儿余习昌、门生王时开写信,与韩愈作《师说》大抵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在这篇《送从子偕王生读书蓝田观序》中,余潜士开宗明义便把读书的目的、意义辩证关系说的十分清楚,他认为“学宜志在圣贤,不宜志在富贵利达”与“吾所志者,不过在富贵利达,其他非所知”,是两种极端。他告诉从子与王生:夫求古人之德业者,非必自居乎贫贱困厄,弃制科文艺而不讲;为今人之驰骛者,亦未必皆能取乎富贵利达。“恃博览能文而无不售,此亦人之所知也”。
其实,圣贤与利达之间,正是余潜士的人生自况。余潜士没有成功走上科举功名之路,但因读圣贤书不意成就其“布衣先生”之名。他常提“谋食”之事,却也念念不忘“谋道”,辗转于二者之间,“终愧未能判然”。
28岁的时候,余潜士从鳌峰书院肄业,受聘于比他年长15岁的同窗高士瀛家的“高氏塾馆”,这是余的第一份私塾教职。在高氏课馆十年,想必从蒙馆到经馆,从识文断句到科举文牍,高家的子侄从余先生处都一一领受过了。高士瀛去世后,余潜士在高氏塾馆的课馆生计也遂告结束。
从卢美松著《余潜士行状记略》一文可知,余潜士40岁以后到60岁之前,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家乡课馆的,作为一名私塾先生,他颇被乡里尊重。他不时为乡民订立《禁盗乡约》《保甲乡约》,受友朋之托撰写寿序等“世俗酬时文字”。
余潜士有两次进京科考经历,42岁那年,以拔贡身份赴京参加廷试,意气风发,沿途作《北游杂咏》诗;60岁那年,他赴北京秋闱,然“试礼部未第”,遂入福州东门魏杰家馆,以教学终其身。
看起来余潜士是通达之人,他虽未能完成更高阶层的跃升,但也始终没有消沉。他随遇而安,对生活现状处置泰然、甘之如饴——不然,又能怎样呢?!
三、
阅读余潜士致弟子、文友、同好之信札,反复体味其课馆授业之精髓。
一是启蒙教化,循循善导;二是寄望后秀,殷殷相期;三是乐育英才、乐道安贫。
在《寄示兄子习昌书》中,余潜士告诫侄儿:学问之途,莫先立志。志在圣贤,则为圣贤门中人;志在科名,则为科名路上人。志切则功自勤。汝年已长大,宜何如猛省也。“无志之士常立志,有志之士立长志”,他常教导弟子“立志”的重要性。
余潜士注重因材施教,他认为习昌“心常放而不收,道义不敌纷华,恐不能闭户内敛。一念外驰,此身将同游骑”,因此,需要“处廖寂幽僻之境,以求至味于无味”。他对弟子王时开的读书志向颇为嘉许,以为时开“或可无迷于所向矣”;但是由于时开“禀质甚钝”,“恐其心之滞而难彻,而所志渐以推磨也”。因此,余潜士希望时开精研古圣贤之道,究其所以,由一至广,可穷可达。
在《答郑东保书》中,余潜士写道:舌耕多年,此心惓惓,唯冀英才蔚起,一乡一邑中有好人物,成学问,立事功,庶几得以撑持山川气运,不至暗淡寂寞。
郑东保是余潜士好友,状元郑性之后裔,家住侯官关源里。余潜士在大穆埕授徒期间,曾便道访问郑东保家,观览郑性之所留朱熹手书《易系传说卦》一幅。郑性之曾从师朱熹门下。儒业后学,自然同气相求。
在《与高生兄弟书》中,余潜士对高生兄弟“颇知发奋用功,私为欣幸”,他提醒高生兄弟“为学以变化气质为先,性气刚拗偏执,此最为害”;“宜知矫克,常自谦谨退让”。
余潜士视私塾课馆为谋道、谋食之业,在《答百书书》中,他写道:阁下谈经授徒,乐育英才,后进中识趣不凡,有志实学者,想栽培多少,得便幸示及一二。平生一点殷殷爱才之念,固结未可消磨,此则可为知己道者。
在《与同里张生书》中,余潜士语重心长地告诫张生,族中训蒙,是贫儒本业,权作谋生之计,当以“天降大任”视之,“思激昂奋发,自不敢颓惰”。针对张生在旧馆授业中所遇不快,余潜士直言“流俗愚蒙,直以情理告之,合则来,不合则去,处之裕如”。他希望张生“愿自今以往,硬着脊梁,踏定脚跟,勿以淡泊为可厌,勿以习俗为难化,勿以学业为可弃,勿以因循怠玩而虚度光阴”。
余潜士是一位私塾名师,饱学诗书,通晓五经;执掌教鞭,教化无数。其《<养蒙故事>自序》一文,颇多心得。“予忝居蒙馆,为句读师者有年,因于经训之外,窃取朱子《小学》善行之类,增集传记故事,日与童稚讲而习之,俾略识古人修身敦行之成迹,分类条例,各系时代,欲其便于记忆也”。仅此,我们便得以窥见余潜士课馆蒙童之用心。
作为一介寒士书生,余潜士“饔飨而岁收馆谷,无他营也”。他在《姑留稿自序》中言:惟读书隐念,耿耿难忘,购书奢愿,时时勃发,古人岂弃我哉!余潜士也自叹:抚老大之年华,而德不立,功不建,天地父母,不虚生此微躯乎!
对着这些文字,我突然便有些感慨心动。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乡土文化大约便是靠着像余潜士这样的许许多多的乡间名贤来维系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称之为“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也正是被像余潜士这样浸淫着传统儒学的文人,以其授业传道精神而不断建构起“彝伦攸叙”的纲常。
我曾在余潜士读书的鳌峰坊、寄寓的宫巷徜徉;也流连于余潜士故居“乡贤第”以及他苦读四年的高盖山。我试图拼出一幅余潜士授课图,那是一种什么形象哦?
遥遥俯仰天地间,一介寒士种春田。
只可惜,我无缘在余师门下蒙学受业!(完)
2025、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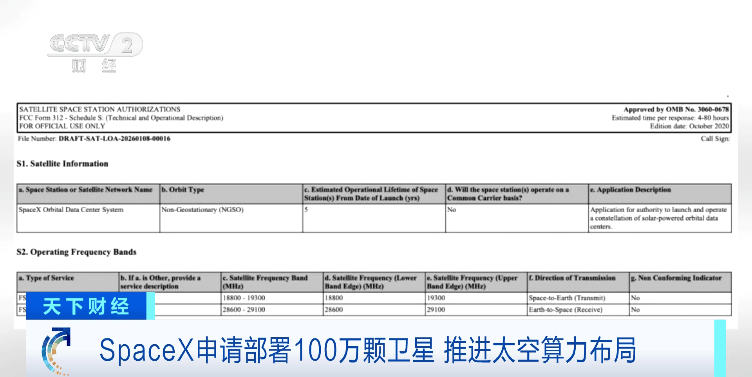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