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1]-乡土生命的热爱与疼痛——张亚明先生《我的萧国我的城》读后-华闻时空](https://hwsk.oss-cn-shanghai.aliyuncs.com/2025/10/image-172.png?x-oss-process=image/auto-orient,1/quality,q_90/format,webp)
作者:雷开艳,一个在文学与朗诵边缘行走的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宜昌市作家协会会员、夷陵区文艺评论家协副主席。
一
评论是件苦差事,尤其是厚重的文字。
张亚明先生的《我的萧国我的城》,我至少读了三遍以上。因为文字太好了——去伪存真、情感淳厚、境界高远、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其既兼有沈从文的诚挚,又兼有陈忠实的神秘。是以,我开始是听(像听广播一样),但是,这个文章太长,一次又听不完,只能断断续续地听。而每次续听之时,它又会影响到我整个的阅读情绪。因此,在动笔想写下此文时,只能是又听又读。一切皆因,我想读出新意,解读好文本。
古萧国城
文字美学与文学表现形式,张亚明先生已经炉火纯青,在此就不加赘述,主要谈谈从我的视角看到先生此文所表达的思想性:
一、小城命运与文明兴衰的镜像
1、附庸小国在强权博弈的历史语境中的悲剧性,隐喻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
2、地理决定论的颠覆提问从自然宿命论提升到制度批判与文明反思的高度。
二、社会现代化进程悖论——悬浮与皈依的精神困境
1、通过一家三兄弟同年跳龙门的阶层跃迁的个体解放意义,但更尖锐的是随之而来的悬浮与皈依的精神撕裂,实则是社会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的心里投射。
2、物质的进步与文化的断根,当游子在都市习惯了觥筹交错的浮华,故乡淡化为精神影像,揭示现代化对文化根脉的消解导致身份认同的虚无。但这又是社会化进程中绕不开的结。
三、贫困经济学:饥饿记忆的权利解构
1、贫困作为系统性暴力,当贫困吞噬生命、精神、理智时,实则是制度性剥夺对个体生命的践踏。
2、饥饿记忆的意识形态批判,先生将父辈的饥饿记忆嵌入国家变迁史,成为时代沉疴的微型纪念碑。
四、文化救赎,重写边缘的史诗
1、通过李茂祥十年面壁修纂县志,当萧县作为中原文化与东夷文化交汇区被重新书写,实则是为被遗忘的文明碎片正名。
2、乡愁在文中体现为双重性,即是萧国望断的情感羁绊,又是凋敝的东西在凋敝的理性认知,这种即眷念又疏离的张力使乡愁超越个人感伤,升华对文明新陈代谢的哲学接纳。
五、存在之思,黄土悲歌中的生命哲学
1、当个体在历史洪流中如草芥般挣扎,其生存意义何在?
2、死亡叙事中的超越性,随蕃远去的生命亡灵的死亡意向与黄河奔流的永恒意象并置,形成生命有限性与文明延续性的对话,这种对死亡的凝视最终转化为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感。
综上:对土地的感恩、对生活的感恩、对苦难的坚忍,早已内化为张亚明先生的故乡情结。皆因于此,故乡虽然是一根线,但却是他的整个世界。
龙城龙河景观
二
一代人有一代人浓郁的乡愁。而乡愁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答案的。且听张亚明先生如何说:“多年来,每每接到乡愁题材的邀约,都曾有过瞬间的激情与冲动,但结果皆因诸多莫名的纠结而搁置。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养过我的故乡究竟是什么?又给我留下了什么?如今又乡关何处?木心说,‘哲学的乡愁是神学’,我的乡愁又是什么呢?”
朴实的文字,不仅灵动行走着,且闪耀着光芒。
我的乡愁又是什么呢?我也曾如此问过自己。我不同于张亚明先生这样的游子。从出生到现在,我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生于斯,长于斯,出嫁也距离娘家仅二十来里。都说女儿家,女儿家,女儿一旦出嫁,娘家便不再是家。婆家呢?又缺乏童年生长的记忆,那些温馨美好的过往不会被复制。而大多数人的童年,是他这一生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我忘不了生我养我的故乡,但我似乎又没有完全融入我现在所处的地方。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嫁在农村,但我又似乎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纯粹的农村人。对生养过我的土地,情感很复杂。我似乎一直想逃离这片黄土,但实际上一直在这片土地上生存。城市不像城市,农村又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农村。我像一个无根的浮萍,在这种虚空的境界里飘来飘去,找不到落脚的地方。于是乎,我那本没有形的浅薄的乡愁愈发飘渺。我甚至担心,它会不会在某一天,被柏临河畔的风无端地吹了去。
“有人说,没有乡愁的土地是苍白的。也有人说,所谓故乡只是少年时光里的记忆,停留是刹那,转身即天涯。”命运既然没有给予我与故乡转身的机会,那是否我应该庆幸,我一直与故乡相依相伴?这二十来里的路程,是婆家与娘家,故乡与他乡的距离。但站在故乡的河流之上俯视,喝的是同一条河流的水;从区域划分,同属一个镇。原来是我的格局太小,我的故乡难道就仅是我从小玩耍的那一方天地吗?我的故乡啊,范围变大了,变广了。这种心情下,我无来由的竟有点“同情”张先生了。
亲情、乡情、土地情、萧城情、家国情。一片目光,走向一段段光洁的文字。在每次展读的时候,它行走的速度,都让我感动。张亚明先生一直执着于乡土关怀、乡土想象和乡土精神重建。其笔下那些行走着的文字,着眼整体,兼顾细节,不仅仅散发出一种亲切雅致的情调,且带给人一种崇高而宁静的感觉,即使某些微小的细节,也常常会有一种震撼心灵的力量,但它落地的重量却超出了我所想像的厚重。它们就像泉水一样清澈,像土地一样深刻,让汩汩涌动的情感,力透纸背,难以释怀。这样的文字在南方初冬的日子里,传递着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可敬的,也是令人感动的。
萧县博物馆
三
曾经的乡村生活,与其后多年的记者生涯,滋养和影响着张亚明先生的写作。
也正因为记者的身份,张亚明先生经见了很多,认识了社会的繁杂和冷暖,这些也成为了他写作的重要素材。所不同的是,张亚明先生笔下的故乡却并不拘泥于他出生的那个小村庄,而是曾经的萧国,现在的萧城。我庆幸张先生在无数次纠结之后,终于找到了宣泄乡愁的出口,而他一旦找到了这个突破口,其乡愁便如大海的波涛一样,翻滚奔涌而出:故乡的风,故乡的云;故乡的梦,故乡的人;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史,故乡的魂;故乡的文,故乡的韵;故乡的情,故乡的问。骨血、精魂。每一个章节,无不是张亚明先生对故乡的深情回望、抚摸与凝视。
写作是作家的天职,同时也是信仰。故,对故乡的爱,如果仅仅停留在高兴欣慰的层面上,未免有些肤浅。张先生在思考,如何“文”与“史”相通,“史”与“理”结合、“辩”与“识”统一的讲好萧县的故事?如何丰富众多景点的人文内涵和民俗元素,让停留纸墨、高居庙堂的萧县史实变得灵动鲜活,以提升扩展萧县的知名度、美誉度?如何汲取萧县历史的精华,“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如何系统打捞萧县历史的秘密,厘清萧县历史文化的“因果链”?如何超越具体和有限,超越现象和碎片,站在更高处理解萧县历史的内在逻辑?如何修复萧县历史的缺环,让萧县的历史光耀现实、催生出新的文明形态?这一个个掷地有声的提问,警醒每一个有良知的人。
实则,张亚明先生的提问从文章的一开始便一个个如连珠般抛出了。
回顾故乡的苦难历史,“天知道,村庄大北地洒满白骨的“杨树林”,令人心悸的“乱坟岗”,到底掩映着多少饿死、病死、吊死的魂灵?”
堂哥问他,“那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如今很多年轻人认为是天方夜谭。你们文人为什么就不能写下来,唤醒人们失忆、迷乱的神经?”
他问自己,也问他人,“为了诗意的“活着”,为着“活着”的诗意,一个个“悲壮”地逃离了故土,流浪异乡;因为灵魂的悬浮,因为悬浮的灵魂,却又渴望心灵的皈依,接近故乡。故乡于我如客栈,我于故乡如过客,这是一种精神的撕裂,还是理性的扬弃?是精神还乡的自我救赎,还是身份认同的文化寻根?”
每一问,如重锤敲打。说什么呢?做什么呢?又抑或,是逃离、坚守、还是改变?家乡的苦难历史深深烙进张亚明先生的记忆,那个饥馑随行的年代,浮夸风的年代,已然造成深深的时代印记与伤害。苦难不愿被翻开,沉睡于记忆的最角落。没有人愿把苦难当成财富,但苦难却如天地永恒般地存在于世。
追忆历史,目睹现实。
张亚明先生能问出这么多的问题,其本身便足以说明先生的才华与学识大大的,真是不得了。所以,先生才能够从各个方面提出这些问题。其次,也说明先生对故乡的那种感情是非常深刻的。如果对一个地方感情不刻骨铭心,那么,先生就不会发出如此多振聋发聩的问题。这又说明什么呢?说明张先生立足于乡土大地,以悲悯之心领略世间万物,且秉笔书写,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农民代言,意在唤起人们内心的良知。因为他所有的问题,你都能看得出来,他不是为自己而问。虽然说也是自己内心的疑问,但是先生放在如此大的平台上,便不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问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凤山隧道
四
故乡是一味药,苦涩,但能治疗乡愁。
这是一个个游子出走离开家乡后发出的心声。如果说,这世界上有一条路是最为幸福也最为难走的路,那么,一定是回乡之路。回乡,首先是精神回乡,而后才是身体。精神回乡,不得不撕开那层层帏幕包裹的思乡记忆。对张先生而言,那每一层布包裹的是带着血泪的沉痛与难言。然我们终将直面,因为我们要知晓,我们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与张亚明先生一起欣喜、欣慰,故乡以全新的样貌出现在我们眼前。“小城无处不飞花,无处不绿荫,无处不优雅。县城成了景区,景区就在县城。人与城,人与自然,在这里演绎着视觉浪漫。”“家在景中悠然栖,人似仙踪画中移”。
战乱的萧国,激荡的萧国;四次迁移的萧城,贫困的萧城,无论是宿命还是历史的幽默,都已远去。那些历史的过往,终究停泊在时间长河的那头。如今的家乡已然蝶变,必将有新的记忆来填充未来长长的岁月。其实,双脚踏上故乡的那一刻,张亚明先生的乡愁便被无限释放了。自然,我也释然了。而我那浅薄的乡愁,必然也会有新的载体,且使之变得厚重,继而长远。读罢先生的文字,掩卷而思:这是一篇沉重、浩大、深远的乡愁记忆,又是满含深情的乡愁展望。评论家李敬泽说,“乡愁是一个人或一个文化对过往的记忆,不仅包含着过去是什么,还包含着人应该是什么,生活里应该有什么,这是乡愁。所以,当我们热爱田园、热爱乡村、热爱大地,不仅仅是因为很多东西正在逝去,也是因为我们认为那些东西包含着在我们生命中非常珍贵的价值。”
其实,李敬泽先生的这段话也可以看作我们每个人与故乡的对话。
凤城湿地公园
五
故乡,无论是贫穷或是繁华,我们都不会舍弃它,忘掉它。它一直存在于我们灵魂的最深处。除此之外,读了张亚明先生的文字,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沈从文的湘西散记系列,二者所不同的是,沈从文所写的是沱江边上的吊脚楼群,而《我的萧城我的国》是皖北。从地域上看,一个在南,一个在北,但在揭示风土人情,生活的真实可信上并无二致。由是,张亚明先生是在为他的萧城和萧城的人民立碑树传之——假如先生没有和他们的血肉相连,没有知心知底的感同身受,是很难将他们的生活现状包括他们的精神世界呈现得如此逼真传神的。故,张亚明先生之《我的萧国我的城》早已不仅仅局限在“小感触”、“小哲理”、“小情小爱”的“小我”状态,而是由点到面的萧国情,扩展到了更大范围内的“民情”、“国情”,物化到“世道人心”、“民族国家”、“天地自然”等宏大主题之中。且最终统一到强烈历史生存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体现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忧患意识。
夫农天下之本也。
萧城精神的核心就是浓郁厚重的家国情怀。遥想着萧国——萧城——萧县,我似乎听见有个声音从遥远的地方隐隐传来。“无论我与故乡离的多远,分别多久,我永远牵挂着故乡,永远是故乡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
萧县县委、县政府办公楼
余记
我本与张亚明先生不熟悉,之所以写下这篇文字,皆因中了津门作家段(家军)先生之“诡计”。十月初的一天,与段先生正闲聊间,他突然发来一篇稿子,且留言叮嘱,得闲了,仔细看看这篇稿子。这样子的事情常有发生的,我也就没太往心里去。但是,当我打开文稿后,仅粗略一读,便被吸引住了。随之,连续多日细读。期间,虽与段先生有所交流,但并未想着写下只言片语。多日后,段先生又留言,且一再强调道:《我的萧国我的城》意见成熟后,要有话说,此文乃我的好友张亚明先生的杰作。
得,段先生一句话 ,我又进了他的“套子”。
阅读这篇文字的同时,我在网上略搜了下张亚明先生。一搜,可是不得了。却原来张先生早已是著作等身的名家。只不过行事低调罢了——大家风范。
春华秋实,周而复始。千百年来,中国农村农民的生活一直是贫困的,贫困是中国历史的情绪,更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实况,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人的精神也总是带着压抑,这种压抑也总是传递般地滞留在每一个人的心头,不管你接受与否。滞留在心头的东西还能不弥漫在山野之中?《我的萧城我的国》是对萧城的俯视、远望,同时也是观念式的扫描,是把历史的萧城全景式地缓慢地推移到读者面前。
叙述历史离不开时间、地点、事件。
要写萧城的历史,必须写它的山野,它的山川河流,它的名胜、古迹以及在这些地方发生的重要事件。在叙述这些时,越是把时间往前推移,所述的历史则越深、越久远;飘散的历史烟尘越古老,承载的岁月越厚重;展现的历史越细致、意义则越重大。
批评家雷达认为:“最有分量和最有价值的文学,应该是关注人存在境遇,展示民族的灵魂和心识的,直指人心的,具有形而上追求的文学。”由是,张亚明先生关于土地、人民历史和未来的思考,并没有停留在忧思的层面上,而是把其他作家思考的终点作为自己思考的起点,深邃的目光穿越层层历史迷雾,表达出对未来的坚定信心。
因此,张亚明先生坚信,中国共产党为民而生、为民而兴、为民而强。实现“中国梦”,关键靠两条:“一靠凝聚和释放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二靠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而这些论述,也无不体现着张亚明先生的“睿智”思想。故而,对萧城山野的眷顾,实质上是张亚明先生恋乡精神的回归,是对萧城人文的关怀和探究。
换言之,先生的文字,亦如錾刻在皖北大地上的一枚枚朱红大印,让人肃然。
2025年10月于夷陵龙泉小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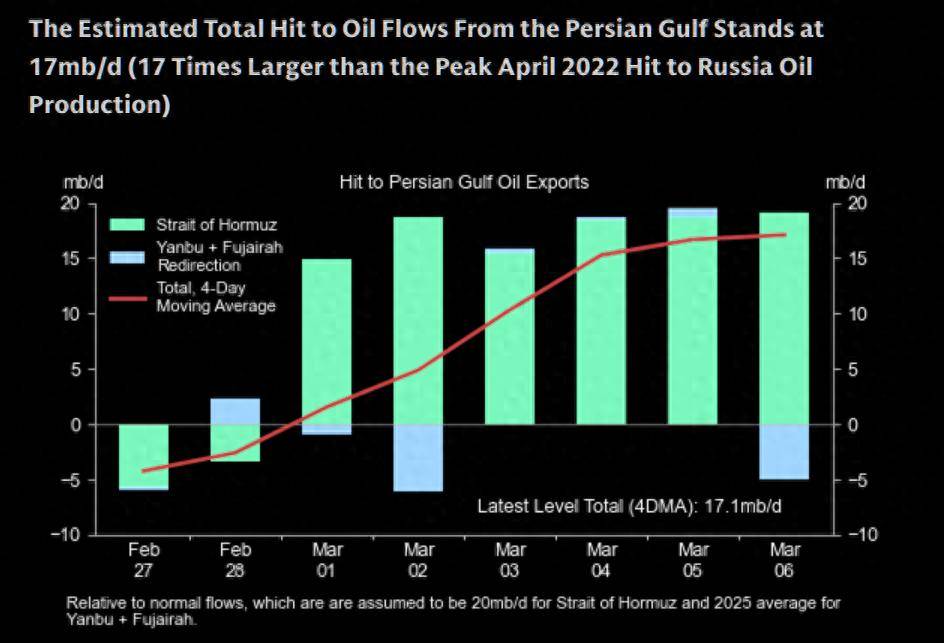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