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考核制度的阴影,如同南方雨季里挥之不去的闷热湿气,沉沉地笼罩在营业室上空。吕主任强调的“零差错”目标,在现实面前显得格外脆弱。尽管每个人都绷紧了神经,压抑了闲聊,专注于眼前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凭证,差错,终究还是像暗礁一样,接二连三地浮现出来。
第一个撞上枪口的是胖大姐。这件事发生在考核制度执行后不久。一笔本该采用信汇方式的凭证,胖大姐在处理时,不知是手误还是当时脑子里想着别的什么,竟然错用了电汇。电汇手续费更高,流程也不同。好在差错很快就被上级行的事后监督中心在日常核查中发现了,通过系统发回了提醒。胖大姐自己也惊出一身冷汗,立刻按照指令进行了冲正和重新处理,及时纠正了过来,没有造成实际的资金损失。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胖大姐暗自松了口气,以为只是虚惊一场,内部改正了就行。
没想到,几天之后,在营业室例行的月度工作小结会上,吕主任板着脸,再次重提了这件事。她将那份来自上级行的差错提醒记录打印件放在桌上,手指在上面点了点:“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了。上级行的月度差错通报马上就要下来了,这笔差错肯定会被当作典型案例列进去通报。我们必须引以为戒!”她的目光扫过在座每一个人,最后落在胖大姐身上,语气加重,“绝对不能出现这样的低级差错!这不是操作水平问题,是责任心问题!”
胖大姐的脸一下子涨红了。她觉得憋屈,忍不住开口辩解:“主任,这事…这事不是已经及时纠正过来了吗?也没造成实际损失,只是流程上用了不合适的渠道。这…这怎么能算正式的差错呢?”她试图强调“及时纠正”这个点。
吕主任立刻打断了她,脸上的表情更加严肃:“纠正了就不算差错了?这是什么逻辑!都已经被上级行在月度通报中点名批评、当作反面例子进行通报了,这样还不算差错,那什么样的才算是出差错?难道要等到资金真的出了大问题才算吗?”她拿起那份打印件,“白纸黑字,通报批评!这就是铁的事实!”
胖大姐张了张嘴,看着吕主任不容置疑的神情,再看看周围同事或同情或无奈或事不关己的表情,她最终把话咽了回去。她知道再争辩也无济于事。大概心里实在憋屈,想想她还是为自己小声开脱了一句,声音带着点沮丧和自嘲:“唉,这么简单的事怎么会犯这种糊涂呢?看来是真老了,不中用了。做得多,错得也就多。真巴不得早点退休,省得在这里丢人现眼碍事……”说完,她低下头,拿起桌上的凭证用力地翻动着,不再看任何人。梅兰看着胖大姐微驼的背影和花白的鬓角,心里涌起一丝复杂的滋味,有同情,也有些许警惕——简单的事,放松了警惕,一样会犯错。
考核带来的紧张气氛并未因胖大姐的“首罚”而缓和,反而像一根越拧越紧的发条。第二个月才刚刚开始没几天,差错再次降临。这一次,是琳姐。
琳姐在营业室里是个独特的存在。她平日里总是讷讷少言,极少参与大家的闲谈嬉笑,仿佛她的世界只有眼前的凭证和账簿。长年累月,同事们总见她踩着上班的铃声匆匆进门,又踏着下班的铃声准时离开,两点一线,生活轨迹清晰得近乎刻板。她的穿着打扮素净简单,常年就那么几件旧衣裳,脸上也极少有大的情绪波动,清汤寡水,悲喜不露,平静得像一潭深秋的湖水,不起丝毫涟漪。有人觉得她这样没意思,活得太过寡淡;但也有人说这样也好,省心,免生是非,日子过得平静安稳。然而就在前半年,平静的水面下却暗流涌动,忽然传出她丈夫同她离婚的消息。那个男人丢下了她和正在上中学的儿子,头也不回地走了。有知情人私下里议论,说她丈夫后来娶的那个女人,论样貌,还不如琳姐好看呢!于是几个姐妹聚在一起时就纳闷了:“你说这男人到底图的什么呀?”随后又仿佛瞬间参透了某种玄机,带着点促狭的意味嚷嚷道:“嗨,这男女之间的事吧,说到底,夜里到了床上,灯一吹,什么都看不见,漂亮不漂亮的有啥打紧?关键是要该硬的硬,该软的软,该做的做,该说的说!光有张脸,木头疙瘩一块,有啥意思?”这些议论,琳姐本人或许听到过,或许没听到,她依旧是那副平静如水的样子,只是眼神似乎比以前更加黯淡,背影也显得更孤单了些。
琳姐的差错发生在第二个月的上旬。当时她负责与县财政局进行月度国库对账。就在当月,恰好遇到上级行国库处临时下来抽查。在检查她递交的对账单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她在送达给财政局的那份纸质对账单上,漏了自己的签章。更麻烦的是,财政局方面返回给银行的这份单据,不仅没有负责人的签名和核对相符的标记,连银行原来预留的印鉴也盖得模糊不清,最关键的是,那个印鉴竟然没有盖在规定的位置区间内。这显然是一份存在多处不规范的对账单。
事后分析,琳姐的责任主要在于:当她拿到财政局返回的这份明显不严谨、欠规范的对账单时,没有按照操作规程将其退回给财政局要求更正或重新出具,而是直接作为有效凭证入账处理了。这种“默认不规范”的做法,在上级行严格的检查下,就成了无可辩驳的操作差错。
当差错确认,并且得知这次差错将与当季的绩效工资挂钩、扣钱在所难免时,琳姐的脸上依然看不出太大的波澜,只是眼神更加黯淡了些。她沉默了许久,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声音不大,却带着深深的疲惫:“我己经尽力了……真的尽力了。每天上班要跟这么多张传票、这么多份账表打交道,数字、印章、格式……一点都不能错。可是……还是出了差错。也许……也许在所难免吧……”这时,上级行检查组正在向支行领导层面反馈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了琳姐的这个差错。琳姐不知从哪儿听到了反馈的大致内容,向来沉默的她少见地又低声补充了一句,带着点不易察觉的委屈和辩解:“其实……也就是一点小差错,小事情……不能小题大作吧?我在这里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
这话不知怎么传到了吕主任耳朵里。吕主任找到琳姐,当着几个人的面,语气带着明显的不悦:“小事情?小事情都干不好,还怎么干大事情?每一个小环节都可能引发大问题!这不是态度问题是什么?”
琳姐微微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捻着衣角,沉默了一会儿,才低声回应,声音里听不出情绪起伏:“我本来……就是个小人物。小人物……也只能干干这些小事情。”这话听起来平淡,却隐隐带着一丝倔强和自弃。
吕主任大概也没料到她会这样回应,愣了一下,随即更严厉地要求她必须端正态度,深刻反省,并要她当众表个态。琳姐抬起头,目光有些空洞地望着前方,最终还是只吐出了一句简单的话:“知道了。其实……我也不想错。这次错了,一定吸取教训,下次会改,一定改!”语气里听不出多少承诺的分量,更像是一种程式化的回应。梅兰在一旁看着,心里有些说不出的感觉,既有对琳姐遭遇的同情,也隐隐觉得这种“尽力了”的无奈叹息背后,似乎隐藏着更深的东西。
然而,差错像是也会传染一样,一旦开了头,就接踵而至。紧接着,娇妹妹也出差错了。时间也是在第二个月,离琳姐的差错没隔多久。那天早上,娇妹妹来上班,从她那张脸孔一看就知道咋天晚上在麻将场上熬的时间过晚了。她哈欠连天,眼泡浮肿,脸上带着熬夜特有的疲惫和苍白,连走路都显得有些脚步飘忽。她强撑着精神坐到岗位前,一边揉着太阳穴,一边打着呵欠,随手接过一家商业银行支行交换员递来的几张支票。其中一张支票的填写日期本该是当月某日,但出票人填写时可能笔误,写成了上个月的日期。按常规,这种远期支票需要特别注意或退票处理。但娇妹妹当时精神萎靡,注意力根本无法集中,审查时只是匆匆瞟了一眼日期栏,竟然没有发现这个明显的、本不应出现的“过去时”日期,就按正常支票处理录入系统了。直到下午,过了截数时间,系统处理完毕,上级行营业部在进行最终清算核对时,才发现这笔交易的日期存在问题,立刻打来电话询问:“这张支票日期不对啊,是上个月的日期,怎么当正常票处理了?错了,当然错了!”娇妹妹接到电话时,才猛地清醒过来,懊恼地直拍自己脑门。熬夜麻将的代价,最终落在了绩效工资上。
瘦菊也没能幸免。她的差错发生在第三个月的中旬。对于一个似乎总与差错相伴的人来说,这仿佛又是她职业轨迹上的一个必然注脚。每一次出了差错被发现,瘦菊的反应都显得特别“诚恳”——她从不推诿,总是第一时间承认错误,态度良好,言辞恳切,表现出深刻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诚恳地承担起责任。她会对检查人员或吕主任说:“是的是的,是我的疏忽!”“我一定改,下次绝对注意!”“您批评得对,我虚心接受!”态度之好,让人挑不出毛病。但令人无奈的是,她就是屡改屡错。梅兰曾听老同事私下议论过,说以往上级行只要来支行检查会计账务,每一次她经手的操作,总能被翻出这样那样、或多或少的问题,要么是印鉴核对有疏漏,要么是凭证要素录入不全,要么是报表数字勾稽关系没搞准……每一次检查过后,整改报告都写得漂漂亮亮,限期内提交。可是下一次检查,类似的问题,或者换个马甲的同类问题,依旧顽固地存在着。分明是整改只在嘴上、只在纸上,根本没真正落实到位,成了典型的“屡改屡错”。
这一次差错落地,意味着瘦菊这个季度的“零差错奖金”彻底泡汤,还要被倒扣钱。当绩效扣罚单下来时,瘦菊心疼得不行,脸都皱成了一团,对着胖大姐唉声叹气:“哎呀呀,这下好了,这个月算是白干了!几百块啊,就这么飞了!接下来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不吃不喝也得省回来……”她抚着胸口,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那几百块钱的损失,对她而言似乎格外沉重。
一旁的娇妹妹听到了,却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她正对着小镜子补妆,头也不抬地嗤了一声,语气轻松地说:“嗨,不就是区区的几百块钱嘛!至于愁成这样?上了麻将桌,我要是运气好,碰一副四对,再回手杠顶开花自摸一把,赢的钱别说几百,翻倍都说不定!能什么就什么都有了,赢回来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心疼啥呀!”她啪嗒一声合上粉饼盒,脸上又恢复了那种娇俏又带点漫不经心的神采。胖大姐看着她俩,无奈地摇摇头,没说什么。
梅兰默默地听着这一切,做着手中的凭证。差错像是一串被点燃的鞭炮,在营业室里噼里啪啦地炸响。胖大姐的委屈辩解,琳姐那平静水面下的无奈与自弃,娇妹妹因麻将熬夜导致的疏忽,瘦菊那诚恳认错却永不改正的循环……还有那真真切切被扣除的绩效工资。考核制度不再是悬在头顶的剑,它已经落了下来,割开了不同的伤口,也映照出各自应对的姿态。营业室里弥漫着一种复杂的、难以言说的氛围,有压力,有懊恼,有抱怨,有无奈,也有娇妹妹那种近乎麻木的散漫和瘦菊浮于表面的痛心。梅兰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也感到困惑。避免差错,真的就那么难吗?她看着自己手中处理得一丝不苟的凭证,更加小心翼翼起来,同时内心深处也埋下了一个问号:这差错不断的局面,到底是因为什么?
六
紧张而压抑的第一个季度考核期终于走到了最后一天。当营业室里最后一笔日常业务处理完毕,空气中弥漫的不是轻松,而是一种等待审判揭晓般的沉闷。季度统计结果清晰无误地显示:整个营业室,只剩下梅兰一个人,还保持着安全无差错的完美记录。
吕主任在核对完最终数据后,当着所有人的面,正式表扬了梅兰。她的语气是肯定的,带着对制度设计下终于诞生了一个“标杆”的欣慰:“梅兰这个季度表现非常出色,实现了零差错,值得大家学习。”然而,这份表扬落在梅兰耳中,却并未激起预想中的兴高采烈。她没有笑容,只是微微低着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桌角。她感觉自己像一个战场上最后的幸存者,环顾四周,同伴们已然“阵亡”,这份孤独的“胜利”非但不能带来喜悦,反而让她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和莫名的尴尬。更重要的是,她敏锐地察觉到,那些平日里相处还算融洽的阿姨大姐们——胖大姐、娇妹妹、瘦菊,甚至相对沉默的琳姐——投向她的目光里,似乎都掺杂了一种难以言喻的意味。她们对她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私下里,或者在她能听到的范围内,她们的话里话外,不再像过去那样带着对新人的鼓励和关照,也谈不上是赤裸裸的嫉妒,但那份似有若无的、带着刺的语调,分明就是挖苦和讥讽,像细小的砂砾,硌得人不舒服。
梅兰去茶水间倒水时,就听到胖大姐在隔壁桌对娇妹妹和瘦菊说,声音不高不低,刚好能飘进她耳朵:“哎呀,幸亏梅兰没错!要不,我们主任这个季度的绩效工资,可就真的同我们姐妹们一样,泡汤咯!”她顿了顿,语气带着一种刻意撇清的意味,“我们这些小人物,按规定扣了就扣了,反正也就这样。可不能再连累我们主任呀!你说是不是?”这话听起来像是在维护吕主任,实则把梅兰清晰地划到了“我们”之外,甚至隐隐有种将她推出去当“靶子”的感觉。
娇妹妹正对着小镜子描眉,闻言嗤笑一声,接口道,声音带着惯有的娇气和不以为然:“梅兰没错,可以理解嘛。反正能多挣那几百块钱呢!我听说啊,她读大学那会儿可不容易,靠的是助学贷款和奖学金才读完的,到现在还欠着一屁股的助学贷款没还清吧?那几百块对她可不是小数目。”她的话语轻飘飘的,却像针一样扎人,仿佛梅兰之所以能坚持无差错,纯粹是冲着那几百元奖金去的,透着一股居高临下的怜悯和轻视。
瘦菊则在一旁掐着手指头算着,脸上带着精打细算的神情,仿佛在核算超市促销的折扣:“这个梅兰,看来这350块是白捞到手喽!”她撇撇嘴,声音不大却足够清晰,“嘿,其实啊,这钱还不都是从我们大家伙儿这儿扣出去的?不过是借个名目奖励给年轻人罢了!”她的逻辑清晰而市侩,脑子里似乎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得失计算,连带着把这份奖励也解读成了变相的“内部转移支付”。
听到这些议论,梅兰端着水杯的手指微微收紧,心里很不是滋味。一股委屈堵在胸口,闷闷的。她并没有因为保持了无差错而感到丝毫高人一等,反而涌起一种莫名的“对不起”她们的愧疚感。在她心里,这些阿姨老姐们,都是自己初入职场时的师傅啊。是胖大姐手把手教她识别复杂的印鉴;是瘦菊一遍遍给她演示系统操作流程;是娇妹妹提醒过她需要注意的细节;连沉默的琳姐,也曾在她遇到疑难时给予过简洁有效的指点。她们教自己入了道,如今却因为自己表现好,导致她们被扣了钱,而自己反而要拿走一笔奖金……这算怎么回事?像是一种无形的“克扣”。她甚至产生了一个极其荒谬的念头:要不……自己也故意出一次差错吧?这样大家的绩效都扣钱,也就公平了,她们就不会再用这种眼神看自己了。但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就被她自己狠狠地掐灭了。她意识到这种想法是多么的荒唐和不负责任!工作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讲人情面子、分钱多少的事。这是责任!是在银行系统里处理真金白银的工作!工作必须认真负责,不能出差错,原则问题决不能含糊,这是底线。更何况,自己还在试用期,这一时期的工作表现,直接关系到是否能顺利转正,成为一名正式的银行职员。这个现实的压力,让她迅速从那种幼稚的冲动中清醒过来。
“好了好了,大家安静点!”吕主任不知何时走了过来,显然也听到了些风言风语,她提高了声音,试图打圆场,“别在这里说什么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话!”她环视了一下略显躁动的营业室,语气转为严肃中带着劝导,“我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建立这个考核机制,奖也好,罚也好,都只是一种管理手段,不是最终目的!我们真正的目的,是通过这种正向激励和必要约束,达到杜绝差错、提升工作质量的效果!”她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我们做会计基础工作的,不能把它看成是每天的简单重复劳动。每一轮的循环操作,都必须是螺旋式的上升!每一次的上升,都要力求有一次质的飞跃!这才是进步的意义。”
吕主任说这番话时,语气是坚定的。但梅兰站在一旁,却从她眼底深处捕捉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和困惑。吕主任大概压根就没想到,精心设计的考核方案实施仅仅一个季度,营业室六个岗位(包括她自己作为负责人),就有四个出了差错(胖大姐、琳姐、娇妹妹、瘦菊),只有梅兰和自己暂时幸免。这三个月的运行结果,显然与她当初设想的“正向激励”效果存在巨大落差。梅兰心里明白,吕主任自己虽然在本季度操作层面没有出过差错,但在考核指标里有一款明确规定:部门里如果超出半数岗位在一个季度内发生了差错,那么作为营业室的主要负责人,她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组织管理责任,当然也要按规定与绩效工资挂钩,更不用说拿什么“零差错”的奖励了。三个月的实践,迫使吕主任不得不自省和思考:光凭冰冷的制度条文来约束人,看来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如何真正引导人去理解、认同并自觉执行落实这些要求。“以人为本”,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是门深奥的大学问。梅兰能感觉到吕主任这份沉甸甸的反思。
到了下午,营业室进入了最紧张的日终轧差结账时段。每个人都高度集中精神,处理着最后的报表和账务核对。就在这冲刺关头,一个意外的消息像投入平静水面的巨石,瞬间打破了凝重的氛围:在初步轧差过程中,发现梅兰经手操作的某个流程环节出现了账款不符,账面上莫名其妙地少了整整300万元!
这个消息如同一针强效兴奋剂。刚才还死气沉沉、埋头苦干的营业室里,气氛陡然一变。胖大姐、娇妹妹、瘦菊几个人几乎同时抬起头,眼神里瞬间迸发出难以掩饰的光芒,脸上压抑已久的某种情绪仿佛找到了宣泄口,一下子来了精神,甚至可以用“雀跃”来形容她们瞬间的兴奋状态。她们交换着眼神,嘴角难以抑制地微微上扬,之前的沮丧和怨气似乎在这一刻得到了奇妙的缓解。
胖大姐第一个开口,她甚至放下了手中的凭证,摇头晃脑,说话变得有板有眼,带着一种近乎表演的感慨:“哎呦呦,看来啊,我老了吗?不!我没有老!瞧瞧,出差错这回事啊,跟老不老真没什么必然关系!年轻人,这不也一样会出差错嘛!”她的话语里充满了某种“验证”了的得意,仿佛证明了之前大家对梅兰的“苛责”是多么的先见之明。
瘦菊则长长地、粗粗地吐了一口气,像是胸口一块大石终于落地,她立刻接上胖大姐的话茬,声音都洪亮了几分:“就是嘛!我就说嘛!大家谁不是一样出力工作?谁又存心想出差错呢?谁也不想啊!凭什么她就能比我们多拿那几百块钱嘛?”她看向娇妹妹和胖大姐,寻求认同,“你们说对不对?哼,这下好了,公平了!”她的“公平论”在此刻显得格外刺耳。
娇妹妹更是愈发高傲地扬起了下巴,她斜睨了一眼还在手忙脚乱查账的梅兰,用她那特有的、带着点慵懒和优越感的语调说道:“哼,那350块的奖励,说到底那是公家的钱,又不是你自己家里的钱,真以为想拿就能拿得那么顺手呀?咱们这些人,扑在会计核算这个岗位上多少年了?没有十年也有八载了吧?就是一块石头,这么些年熬下来,也该长出青苔了!她一个刚来的小姑娘,一来就想超过咱们这些老姐妹?呵,不成熟,太幼稚了!等着瞧吧,今后有她哭鼻子抹眼泪的时候呢!”她的话语充满了对资历的强调和对新人“冒尖”的不屑。
“哎哎,你们少说两句好不好?事情还没完全弄清楚呢!”琳姐皱着眉头,声音不大但清晰地劝阻道,同时伸出手指,略带担忧地指了指不远处趴在桌子上、脸孔涨得通红、正急得直冒冷汗的梅兰。
此时的梅兰,感觉全身的血液都涌上了头顶,脸颊火辣辣的烫。冷汗顺着她的鬓角和后背往下淌。她大脑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念头在疯狂叫嚣:不可能!怎么会错?错在哪里?她像疯了一样,手指颤抖着,不停地翻阅着今天自己经手的所有操作流程记录、原始凭证和电子表格,一行行数字、一个个印章、一项项记录,反复核对,眼睛酸涩也不敢眨一下。可是,无论她怎么看,怎么算,都没能发现那该死的300万差额究竟是从哪个环节漏掉的,又错在了哪里。巨大的压力和同事们的冷嘲热讽让她几乎窒息。
无奈之下,她猛地站起身,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跌跌撞撞地冲向隔着一道玻璃门的主任室,她需要立刻请教吕主任!也许经验丰富的主任能一眼看出问题所在。可是,主任室里空空如也。隔壁办公室的同事告诉她,吕主任下午去参加支行紧急召开的党组扩大行务会了,据说支行党组正按照市分行(中支)党委的最新安排,部署一项非常重要的主题教育活动,所有中层必须参加。希望彻底破灭了。梅兰的心沉到了谷底。
墙上挂钟的指针无情地走向下午四点。上级行的网络维护系统每天下午四点半就会准时停止运行,所有日间业务处理入口关闭,这意味着留给她查错纠错的时间窗口只剩下不到半个小时!看来,出差错被处罚,已经是板上钉钉、无法挽回的事了。功亏一篑!巨大的沮丧和无力感像潮水般淹没了梅兰。她低着头,失魂落魄地走回自己的岗位,瘫坐在椅子上,感觉浑身力气都被抽干了。
就在这令人绝望的时刻,营业室的内线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靠近电话的胖大姐顺手接起,“嗯嗯”几声后,脸色变得有些古怪。她放下电话,清了清嗓子,用一种混合着难以置信和些许尴尬的语气,对着整个办公室宣布了另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呃……那个……刚刚接到上级行清算中心电话……梅兰那个账款不符的问题……查清楚了……她那边流程没错……是货币金银股那边漏递了一张300万元的入库账单!责任在他们那边。梅兰没出差错。”
这突如其来的反转,像一个急刹车,让营业室里刚刚升腾起的兴奋和议论瞬间停滞。空气仿佛凝固了。梅兰猛地抬起头,怔怔地看着胖大姐,几秒钟后,才像终于卸下了千斤重负一样,长长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整个人几乎虚脱般地靠在了椅背上,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然而,与她这如释重负的反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胖大姐、娇妹妹、瘦菊几人脸上的表情。她们脸上的兴奋和刚刚流露出的“胜利”光芒瞬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难以形容的沉寂。没有人再开口说话,没有人为了这个乌龙事件最终没有伤害到梅兰而感到欣慰。胖大姐低下头,迅速翻动起桌上的凭证;瘦菊撇了撇嘴,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冷哼;娇妹妹则面无表情地转回身对着电脑屏幕,下巴依旧高昂着,但那份刻意的高傲此刻显得有些僵硬和不自然。
整个营业室里弥漫着一种浓重的失落感,一种空欢喜一场后的巨大空虚和更深的隔阂。只有琳姐,在短暂的沉默中,不易察觉地轻轻叹了口气,目光掠过梅兰,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随即也低下了头,继续她未完成的工作。梅兰感受着这片令人窒息的沉默,刚刚放松下来的心,又一点点被冰冷包裹起来。那350元奖励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一座无形的屏障。
图片由AI生成
作者简介:
符浩勇,男,汉族,海南省屯昌县人。现居海口,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曾任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在《人民文学》《当代》《清明》《天涯》《小说界》等文学报刊发表小说800余篇。著有长篇小说《四英岭人家》,中短篇小说集《苏醒的腊月》《夏日里的最后一趟班车》诗集《城里没有故乡的月亮》等28部。曾获海南省南海文艺(文学)奖、第六届全国小小说“金麻雀”奖和《小说选刊》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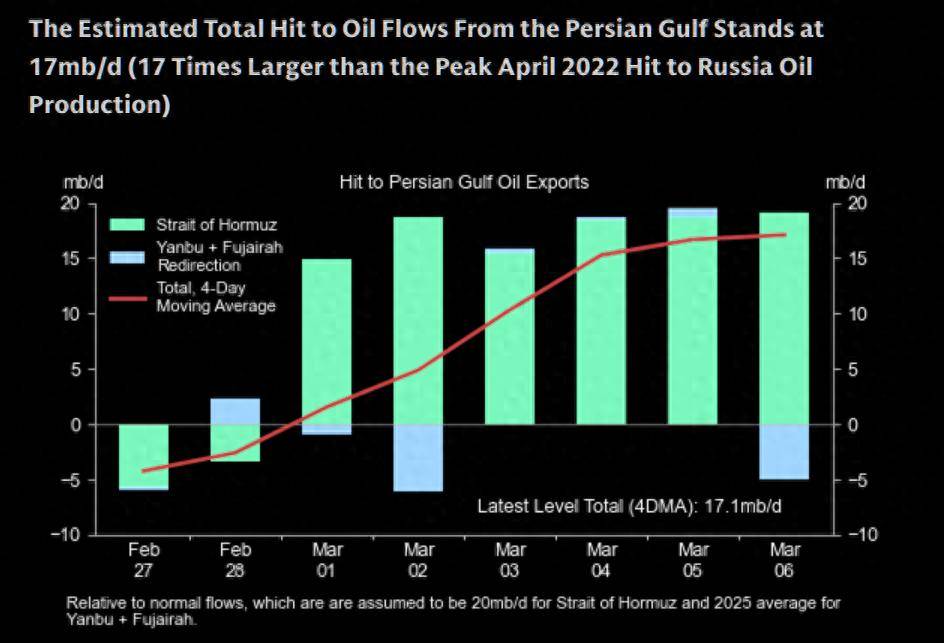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