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俊
南京市人。苏州大学文学学士(1986),南京大学文学博士(1991)。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受聘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暨南大学海外华文文学与汉语传媒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兼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副会长,江苏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曾在美国格林奈尔学院(Grinnell College)、加拿大滑铁卢大学(University of Waterloo)、台湾大学、香港大学等校做访问学者或任教。著有《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世界华文文学整体观》《情与美——白先勇传》《越界与交融:跨区域跨文化的世界华文文学》《复合互渗的世界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历史·记忆·语系》等论著多种;译有《台湾文学生态:从戒严法则到市场规律》;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导引》《跨区域华文女作家精品文库》《海外华文文学读本·中篇小说卷》等;参编《海外华文文学教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等。两次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研究》等国家社科及教育部项目多种。
小城故事
原刊香港《文综》2024年夏季号,感谢作者授权推送。
谁没个童年?谁的童年还能没些个往事?童年是一个人的底色,有什么样的童年,就有什么样的人生基调。我大部分的童年时光是在一个小城度过的,“童年往事”中有很多“好玩”的故事,都与那个小城有关。
一、上学
我上学算是早的,六岁老姨就帮我报上了名。与一般的孩童不愿上学不同,我很渴望上学,对未知的学校充满了期待。上学就要置办“行头”,我们那个时代店里卖的制式书包属于“奢侈品”,一般人都买不起而且好像也没那个必要,我同学的书包花花绿绿五花八门什么形状都有,印象最深的是有个女同学书包竟然是红色的椭圆形,煞是吸引眼球。我的书包是老姨帮我缝制的,蓝色布面,长条形,斜挎在身上自我感觉气派大方很神气。铅笔盒是买的,记得盒盖上是个头裹羊肚毛巾的农民(如今想来大概是以陈永贵为模特)左手执钎右手举斧,正在笑容可掬地开荒种田——背景则是一片金黄的层层梯田(是大寨的虎头山吧)。打开铅笔盒,老姨已经帮我买好了铅笔,笔芯有粗有细有深黑有淡黑什么B1、B2,还挺讲究,橡皮擦是薄薄的一个白色长方块(大概到了三年级橡皮擦已升级为一种香橡皮,有各种颜色可供选择,看上去有点像今天的果冻,闻上去有股香味),令我感到惊奇的是居然还有一个铅笔刨子,是个立体的长方形,厚度中间有个圆洞,铅笔塞进去转动,固定在表面的一个小刀片就会卷出铅笔的“刨花”,就这么转下去渐渐地铅笔就削尖了。
上学生涯对我来说是愉快的,我成绩很好,和同学相处融洽,特别是我的字总能得到老师的表扬——小学时代“抄写生字”想来大家都熟悉,老师布置的作业往往就是一个字要重复抄写几行,如果写错了“罚写”,那就很可能要抄写一页乃至好几页。我的字因为写得好,总是被老师拿来做范本亮出来给同学们看,这让我颇为自豪,也收获了若干崇拜者,其中有个胖姑娘,读小学了却还是婴儿肥得厉害,看上去憨憨的十分可爱,她那时最崇拜我了,我的作业本一发下来她就要拿去“学习”,为了写好字,她甚至愿意用三杆铅笔换我用过一半的铅笔——可能她觉得我字写得好,是因为书写工具有什么特别之处吧。
我上学读书的那会儿,学校时不时地会组织“野营拉练”,每到这个时候,学生都要打上背包,扛着红缨枪,徒步走个十里八里。红缨枪需学生自备,背包也是从自己家里拿个小被子,用背包带子按照打“背包”的样子打好。我的红缨枪是老姨帮我做的,过程颇为繁难:先要找个木块制成枪头,再来要有个适合的枪杆,在枪头和枪杆之间的红缨最为关键——要不怎么叫红缨枪呢?而且,枪杆也不能是“白蜡杆”,还必须漆成红白相间的盘旋纹。为此,老姨绞尽脑汁,终于帮我制作出了一杆红缨枪——枪头是请一位朋友在工厂用机床“车”了一个,红缨是用红毛线再新染出了个新而成,最记得她在漆枪杆时,先用两指宽的条纸沿着枪杆盘旋上去,包好后在枪杆上刷上红色,漆好后取下条纸,等红漆干了,再用条纸包住红色,用白漆再刷一遍,取下条纸后,一杆红白相间的盘旋纹枪杆就做好了。因为老姨在制作枪杆时我在边上全程观看,所以至今记忆犹新。我的这杆红缨枪拿到学校非常拉风,好几个同学恨不得跟我“换枪”——我当然是不会跟他们换的。
张爱玲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上学的路上迟到,会突然觉得周围出奇的安静——这样的体会我就有过。那次学校要外出“拉练”,我睡过了头,匆忙间急急出发,向学校一路狂奔,以往上学路上经常会遇到的同学,此时一个也没有,小城的石板路就是那么“静荡荡”的无声无息。上学多年,我从未对迟到有过如此巨大的恐慌,生怕“拉练”的队伍已经离开学校出发了,那我就真的是“掉队”了。急乱之间身后的背包也散了架,于是只好一手攥着红缨枪,一手拢住凌乱的背包,狼狈地冲向学校。进了校门,才发现全校师生都还在操场上整队,熙熙攘攘颇为嘈杂,可是我在进校门前,居然一点声音都没听到。
为什么会在那时感到整个世界都没了声息?虽然张爱玲的文章使我知道了这不是我一个人会有的“感受”,可是那天的安静给我造成的强烈冲击,至今难忘。
二、玩具
现在的孩子玩具都是靠买。买来的玩具花样繁多制作精美,什么变形金刚遥控汽车,很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在我小的时候,是没有这些玩具的,想要玩具都得自己做,自己做的玩具虽然与现在的“高大上”比起来差得远了,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有成就感有乐趣啊。
我们那时候的玩具,品种倒也不少:弹弓、滋水枪、小惯炮、陀螺、弹子车……,都是“自己造”。我印象最深也最喜欢玩的“自己造”玩具,是链条枪。
链条枪的制作工艺,都是靠手教口授得以“代代”相传。“自己造”链条枪颇不容易——不但材料不容易找,制作也十分复杂。首先你得弄到十来节自行车上的链条,有了链条,你还得找到粗细适中的钢丝,以及黑胶布、像皮筋等,有了这些材料,你还要有老虎钳、锤子等工具,所有材料、工具都齐备了,你还得会“做”会“造”,这一切对于儿童青少年来说,每一种材料每一个过程都不容易——说真的,“造”一把链条枪,没有两把刷子还真不行。
先找链条。虽然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年代,自行车遍地都是,但是你要找个十来节链条,门都不知道在哪里。这就得向“有办法”的小朋友求助,这些“有办法”的朋友只要愿意帮你,总能神秘兮兮地帮你搞到(什么来路你就别问了,这是规矩)。有了链条,第一步需要将串联啮合在一起的链条分解开来,分成两组,一组三节,一组六节或七节,用黑胶布分别缠好,这一切搞好了,第二步就要用钢丝“盘”个手枪架子出来,有了手枪架子,还要用钢丝做出扳机和撞针,有了“枪”的基本组件后,再将两组链条的一排孔口(链条在串联啮合的时候是由一种特殊的“插销”链接在一起的,敲掉“插销”之后,每节链条才会分离开来,并且每节链条上都会有两个孔洞),穿在手枪架子的枪首部位,并将一组长链条(六或七节)用黑胶布固定在枪首后部,短的那组(三节)链条则可灵活掰开左右转动置于前部,在扳机和撞针都安装好后(撞针长度略长于那条长链条组合),用像皮筋勒住撞针,将其搭在扳机的上方,只要扣动扳机抬起撞针,撞针就会在像皮筋的作用下,沿着长链条组合的另一组孔口向前击发。
有了枪,“子弹”是什么呢?火柴。枪“造”好后,枪首前面一组可转动的短链条组合,就成了“弹匣”,将其扳开,把一根火柴从非固定的一组孔口推入(无火药的一头对向前面),然后将其扳回,与后一组的链条组合孔口对齐,链条枪就“子弹”上膛了 ,此时只要扣动扳机,撞针击发装在“弹匣”里的火柴,就会发出“啪”的一声(晚上还能看见火光一闪),火柴也会应声而出,射出“枪膛”。
可以说当年我周围的男孩子,无不以拥有一把链条枪而自豪和骄傲,特别是要成娃娃头,这几乎是“标配”——在玩“打仗”游戏的时候没个枪那还能叫“头”吗?不要小瞧了这链条枪的威力,听说曾有拥“枪”者不慎击中玩伴眼睛致其失明的。这样的玩具在今天看来无疑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并不适合少年儿童玩耍。可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少年,就是在一个粗放的环境中“野蛮生长”的,玩具从生产到使用,都充满了一种“野性”。你可以说这些玩具不文明很危险,然而今天在“温室”中长大的孩子们,他们那些“高大上”的玩具,与我们那个时代的玩具比起来,太过“文明”也太过精细,玩起来或许也有乐趣,但要讲动手“自造”的乐趣和“野性”的成就感,那就没法跟我们比了。
三、游泳
我小时候差点淹死。据说“大难不死”会“必有后福”——此话不知真假。
那年我八岁,在小城和外婆、老姨生活在一起。外婆家所在的小城有条大河穿城而过,小城里的人淘米洗菜洗衣服刷马桶都在这条河里。有河,游泳之风就盛,每到夏天,河面上少不了许多浮来漂去的小黑点(人头),当然免不掉地,每年也总会有小孩不幸溺亡的消息在小城不胫而走。
那时我还不会游泳,不过社会上对游泳很是重视,特别是到了“毛主席畅游长江”纪念日的时候,都有大型的游泳庆祝活动。每到此时,河面上游泳的队伍能绵延好几公里,一路上水面浮动着巨幅的毛主席像、各类标语如“热烈庆祝毛主席畅游长江六周年!”“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以及迎风招展的大红旗和各色五颜六色的小旗子,这些浮动的领袖像、标语及旗帜,均有木制基座,由游泳者或肩抗或手推且游且走,行进途中不时还有阵阵口号响彻云霄,在游泳队伍的前面有先导船,救生小划子则分布队伍两侧,场面十分壮观,非常震撼。
面对这样激动人心的场景,少年情怀不可能静如止水。最初我和小伙伴们还只是在大人的带领下在岸上兴奋地观看,后来“年岁渐长”,慢慢地就有了找机会乘着热闹下水一试的念头。很快,机会就来了。
又是一个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的纪念日。河岸边渐渐地热闹了起来,人们都往河边跑,“快来了”、“快到了”的欢叫声不绝于耳。由于河里每年都会有悲剧发生,所以大人对小孩的管控十分严格,外婆和老姨是绝对不允许我一个人去河边的,更别说下水了。可是那天巧了,老姨去上班,外婆在午休,我偷偷地拿了一条毛巾溜出家门,和约好的同学一起向河边奔去。
小城河边的“码头”是用条石砌就,成阶梯状从岸边逐渐没入水中。我和小伙伴不会游泳,脱了衣服就在码头上趴到水里,用手扒住码头的阶梯,头露出水面嬉戏——也算是“游泳”了。我们一排几个同学这样趴在水里自己高兴,却“占用”了要在河边淘米洗菜洗衣服的阿姨们的空间,地方不够用,正好又有一位阿姨要来洗衣服,于是为了给她让地方,我就向边上挪了一下,就是这一挪,出事了。
虽然码头以阶梯状伸入水下,但它的宽度是有限的,在其直立的两边尽头,和河岸的斜坡形成了一个夹角形的深水区,其时我就趴在码头的边缘,只是在水中自己没在意,当我为阿姨让地方的时候,我扒着码头石阶的手平行着向边上移动了一下,结果一移动我的一只手就落空了,随即身子一歪,就下了深水。
下去以后一定是挣扎了,我只记得我的身子在翻腾中一会儿浮起一会儿落下,浮起时有过蓝天白云岸边垂柳稍纵即逝的印象,落下时就在黑暗中大口喝水了,就在我瞎扑腾渐感乏力之际,一只有力的大手一把就将我拎了起来,接着又有几双手将我接了过去,放在了一只船上——原来是游泳队伍到了目的地回返,先导船看到了水中的“异常情况”,船上的“叔叔们”将我救了下来。
事后听一起去的同学说,是他们首先发现了我的“失踪”,吓得大叫起来,而码头和岸边的大人们一开始看我在水中载浮载沉,还以为我会游泳,后来发现情况不对,才向路过的先导船呼救,总算没让“悲剧”发生。
挨批评是跑不掉的了,不过外婆和老姨看我那副“惨象”也不忍过多指责,倒是庆幸我“命大”运气好,正好赶上了游泳队伍返程,遇到了专业的救生员——感谢那些至今不知姓名的救命恩人!因为有他们出手相救,我才有机会延长了半个多世纪的生命,并在“大难不死”后的近半个世纪,居然毫无心理障碍地,真的学会了游泳。
人的生命其实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正在“实践”的当下人生,另一部分则是曾经“走过”的从前回忆。随着年龄的增长,前者日渐缩短而后者越发延长。“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孩童在成长的过程中既充满了无数惊喜,也与各种意想不到的“潜在危险”相伴同行,只不过儿时并不自知,在懵懵懂懂的状态下,兀自生长着,茁壮着。当渐趋老境蓦然回首,你才会发现,在你童年觉得“好玩”的时候,原来有那么多危险曾经贴近过你与你擦身而过,而正是那些隐含危险却也“好玩”的“童年往事”,塑造了今天仍在“实践”着的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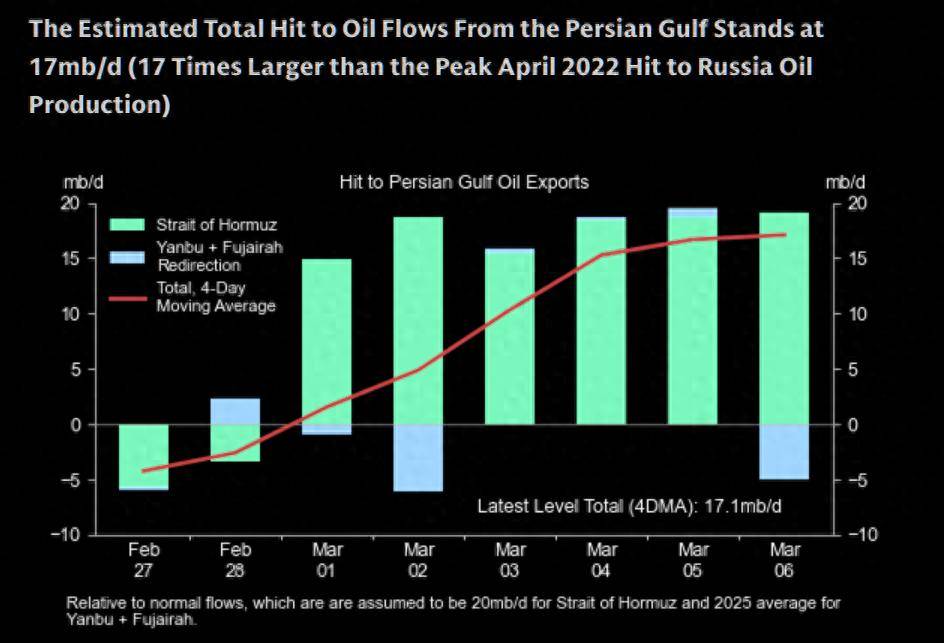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