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多年的“红军隐身人”(第5节)
“白娃死了,又不是我害死他的!”不露面的肖建顺回来了,扛一把锄头,理直气壮,去挖坑埋白娃。他终于去了一块心病,不意却患了一场身病。白娃死后二年,肖建顺也于1947年病故。
苦难,一茬又一茬;于都河水,瘦了一圈又一圈。
平滑如镜的于都河水,年复一年映照着世事。华可英日日来河边捶衣,也把长恨短痛,和泪挥洒河中。“家战”结束,并非好事,也许是更坏的事。原本她有两个男人,如今一个也没有了。逝者如斯,无怨无恨。默默地,她挑起了一个穷家的担子。
穷家,意识味着一切深重的苦难。
过去,她望着于都河水流泪,如今,泪水流尽,繁重的家庭重负,压得她抬不起头。
没有一个熟人,没有一个知已,只有这条江流与其相识,面对一去永不回头的江水,她无限感叹: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一段流血的历史,也即一块流血的伤疤。这是不能述说,不能触动的。
她似蜗牛,驮着一个隐私,一块隐痛,默默地爬行。
1949年,新中国建立,土地改革及一系列政治运动,似一股股巨大的旋风搅动着华可英的生活。由于她对共产党的认识基础,她在普选中任芦山乡选区代表(当时梁国材任乡政府文书)。1953年,她曾任互助组长,1955年任初级社农业合作社社长,1958年曾任高级农业合作社妇女主任,后任西郊公社芦山大队妇女主任等职务。她隐瞒历史,竟然躲过了严格的“政审”关,并被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各级组织瘫痪,她安然无恙,在家中带小孩。
“文革”,对于底层人民来说,就是揭露隐私,在灵魂深处暴发革命。
隐私,成为罪证,成为人们最感兴趣的东西。那时,有的革命组织直接标以:“揭老底战斗队”、“挖定时炸弹战斗兵团”、“剥画皮战斗小组”“”,有些运动的名称直接叫做:“四清”、“三查”、“说清楚”、“清理阶级队伍”。
政治炸弹,随时随地,此起彼伏地在你身边爆炸–一眨眼间,许多好人变成了“坏人”;一些公开的共产党员,变成了隐蔽的国民党员;平日和蔼可亲的老人,现出“特务”、“杀人凶手”、“叛徒”的原形……子女揭露父母,兄弟反目,夫妻分家,谁也不可信,不可靠,人人芨芨可危。
华可英仍披着“兴国人”的外衣,小心翼翼,躲避各种政治流弹、运动扫荡。
不知道,有没有谁躲过了那场“揭”难,华可英终究没有躲过,其四十多年“兴国人”的“画皮”被剥去。对于她,这倒未尝不是件好事。
冷宇宙,龙门县的县长,在“清理阶级队伍”、“三查”中作为叛徒、特务揪出来了。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有一段历史没有证人。没有证人就是不清白,就是“叛徒”、“特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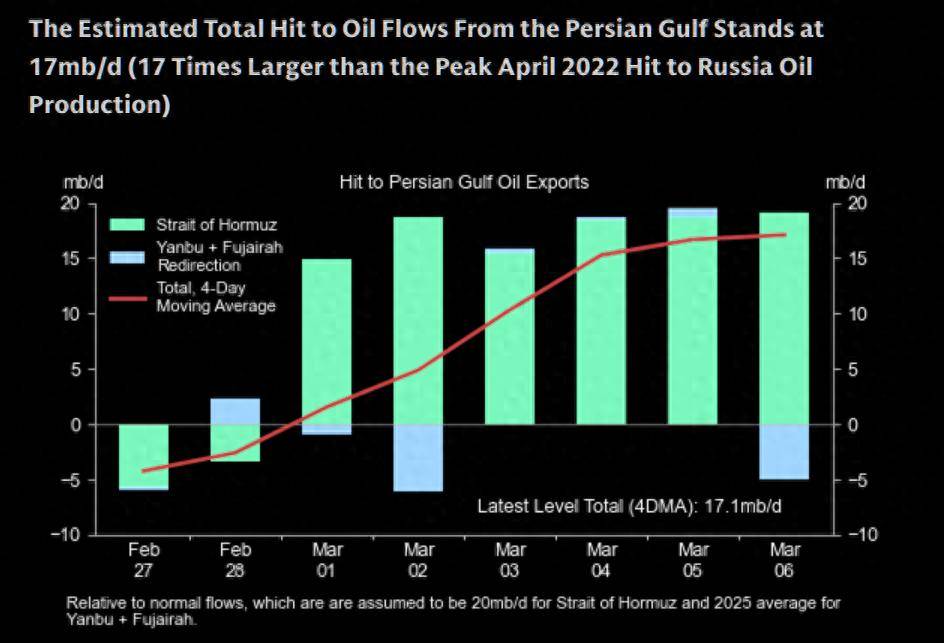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