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作家张浩文先生签名的《绝秦书》后,我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
封面文字告诉我,这是一部写民国十八年年馑的书。这段年馑,我小时候就听祖母和父亲说过,父亲的哥哥和弟弟在这段年馑中都没有能逃得过来,村里的家谱也记载着年馑中饿死了好一茬人。
史料记载,民国十八年旱灾是陕西近代史上最惨烈的年馑。当时陕西人口不到千万,饿死三百万,逃亡三百万,“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干旱波及整个大西北,死亡总人口高达近千万,堪称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一场巨大的灾难。
陕西自古称秦,对陕西来说,这场年馑就是一场“绝秦”的大事件。《绝秦书》为人类记忆下这段心酸史,警示后来人思索生命的苦难之重。
我是没有受过饥饿威胁的人,很想知道生命面对死亡威胁的情景,细细品读,掩卷感慨:生命原来是这样的脆弱与无奈,人性竟然是如此的残暴与卑劣!面对国人“一富必奢”的浮躁民俗,油然钦佩起作家张浩文以记忆灾难警示人性的高远文学匠心来。
张浩文先生以1929年的蒋、冯、闫军阀混战为大历史背景,把笔锋深入进关中平原的绛帐镇周家寨村,盯住周克文家族,深刻解剖了这群平民百姓的苦难史及其在灾难面前人性的无常。
故事是从土匪抢劫周克文家明德堂开始的。社会沉入了兵荒马乱的时代,“土匪如篦,军队如剃”,政府指望不上,成立护院队是民间大户唯一的自保选择,可在那个“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年代,农村的社会治安靠自保自然是力不从心的。再说,抢明德堂还是大烟惹出的祸,本来“民以食为天”,土地用来种粮食是天经地义的事,可那个年代,民间种烟成风,鸦片成为军队、土匪占地为王的硬通货、抢手货。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作家张浩文以敏锐的思想穿透力,看出来那个社会的离经叛道,是酿成民国十八年年馑扩大成灾难的导火索。
第一个触疼我灵魂的是“生命之轻”。面对干旱,一群仁义道德之辈竟然拿两个娃娃的生命去祭祀龙王爷求雨。绛帐镇上,饥民的尸骨遍野,社会救助机能瘫痪,商会仅仅出于怕影响生意才勉强组织收尸,生命毫无尊严,中华文明在这个年馑里沉沦。
面对饥饿,卖儿、卖女、卖老婆比比皆是,儿子单眼就能够把亲生父亲炖肉吃。读到这里,除感叹国人的愚昧、残忍之外,更感叹这哪里是“上天不仁” ,分明是人祸作祟!
“人相食”在《三国志》《水浒传》里就有,《绝秦书》又一次给国人昭告了这一血腥与恐怖,人将不人,是年馑催生了人的兽性发作。
人祸大于天灾,在《绝秦书》的文字里,我似乎听到孔夫子“苛政猛于虎”那遥远的呻吟。西北军政府的头等要务是打仗,不但无暇赈灾救民于水火,反而更加横征暴敛让百姓雪上加霜。专治政府封锁灾情消息,不仅让灾民得不到国际社会应有的救济,甚至为阻止中央军进攻,不惜炸毁铁路,阻滞救济物资的运输。从冯玉祥、宋哲元到孙县长、刘营长,他们打造成一股庞大的战争机器,演绎着肆无忌惮的人间杀戮。刘镇华、党拐子、花豹子、旱地龙,这些军阀、土匪,无时不在蹂躏着老百姓,三秦大地一时回归于乱世春秋礼崩乐坏的野蛮时代,人祸与天灾交织一起,三秦大地怎能不“绝”呢?
族长周克文是周家寨中国道统的化身,饱读史书,礼仪斯文,耕读传家,发家致富,是作者刻意塑造的中国乡村守正农民的典型,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代表,在大灾面前,他个人是清醒的、也是智慧的,却也是无能为力的。在发家致富、面对匪患、率领饥民抗税、舍子保粮、最后赈灾放饭等大事件中,都彰显出了他仁义的理性光辉,可在一场虔诚的求雨闹剧中拿两个娃娃的生命去祭祀龙王,愚昧残忍中彰显出藏在道统骨子里的虚伪,这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大灾面前连自己的同胞亲兄弟周栓成也不顾,人情淡漠令人唏嘘。不过,在中国千百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氛围中,民性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也可以理解,但士神阶层的退化、民性的一盘散沙,确实也促使了这场年馑愈加严重。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也没有回避道统遭遇年馑的无能。
《绝秦书》中,基督教会参与了赈灾,饭本是不分洋教、土教的,但被道统愚化了的周克文却不能容忍,年馑里饿不死才是硬道理,一伙吃基督教会舍饭的儿童,并不买周克文的道统账,国人的迂腐不堪,不能不说也是年馑的孽障。
倾巢之下安有完卵。年馑中,周克文的自身命运结局同样悲惨,他因粮得福,也因粮遭殃,二儿子周立功、三儿子周立言都是因粮丧命的,他自己也被势不可挡的讨饭滚滚洪流所淹没。
弟弟周拴成的赛仙堂,是作家刻意与哥哥周克文明德堂的比照,很难想象,中国农耕文明的传统价值观会溃败成那样,清朝大臣林则徐流血禁止的鸦片,竟然会在民国年间再次泛滥成灾!周拴成伙同儿子周保根一起在绛帐镇开烟馆,谋暴利,迎合三教九流。其实,农人丧失农业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根,烟不能当饭吃,面对年馑,儿子怀揣大烟去换粮没有回来,老婆饿死了,处于生存无望的周栓成,自行钻进棺材,自行盖棺寿终。
周拴成是农耕文明生活退化的一位典型,作家在警示后人,如果人人懂得抓住粮食生产,那才有可能避免年馑。
人有生的本能,人也有死的本能,比起那些仍在绛帐镇城壕里横七竖八的饥民尸体来,周栓成总算死得聪明,这是作家的绝笔。
《绝秦书》以大量的笔墨写周立功和引娃的故事,这是两个在年馑中还有点人性温度的年轻人。周立功在京城读过书,得到过新思想的启蒙,他怀着一心改造乡村的美好愿望回乡,可推行“男女平等”的第一件事就失败了,他的“婚姻自由”受到“三钢五常”传统道德的不齿,他与引娃的自由不幸被抓,受到族规的惩罚,他爹救子代他受过,他无颜再见江东父老而出逃。他又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揭露省府禁烟不力,却没想到地方政府也禁止不当言论,判为死罪,倘若没有那位兵哥哥,也就成为不明不白的屈死鬼了。他选择“实业救国”开办纺织厂本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可年馑彻底搅和了他的美梦,一直疼爱着他的引娃,为给他筹钱办厂,不惜卖身替死。他为筹一笔开办费,回老家向父亲借粮,最终却惨死在兵祸里。
周立功所代表的方向是正确的,可面对千疮百孔、病魔缠身、既庞大又腐朽的社会,靠个人奋斗显然是没有出路的。
读到引娃卖身替死的情节,很难理解作家的用意,细细琢磨,那是引娃走投无路了,那是引娃对眼前的社会绝望了。 这个被亲生父母遗弃,被养父母当长工使唤,被她爱着的立功哥哥冷漠的人,她心力是皆瘁了,正好能遇有机会替罪犯玉堂春去死,“视死如归”引娃是做到了,做的还如此坦然,这是作家的又一绝笔。
周立德是为仗家势去当兵的,因为这是一个有势就有安全的奇特社会,打仗、杀人是他周立德的职业,这是周家寨唯一活过来的人,小说结尾,他从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了西府战役。可命运的归宿是他没能为明德堂这个昔日的家壮起势来,周家寨消失了,明德堂也消失了。
读完《绝秦书》我不由感叹:一个不敬畏生命的族群,就只能在暴力循环中匍匐。
《白鹿原》是一部国人内斗的血泪史,《绝秦书》是一部国人遭遇年馑的血泪史,这两部作品都是陕西文学的杰出成就,异曲同工,意义深远,作家究竟是为唤醒点什么?
作家张浩文在后记里说:毕竟文学是形象的呈现而不是理论的宣示,这部作品意旨的薄厚简繁只能让读者去判断。
我踅摸《绝秦书》,写了这段读后感。
掩卷之后,我回味着、咀嚼着、思考着,只有尊重生命, 方可减轻生命的苦难之重!
2019年6月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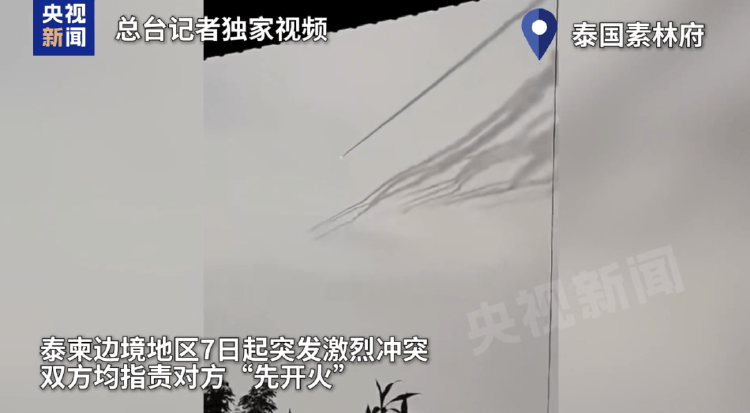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