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艳
![图片[1]-在困境中的挣扎和逃离——读裘帕·拉希莉的《低地》-华闻时空](https://hwsk.oss-cn-shanghai.aliyuncs.com/2025/07/image-108.png?x-oss-process=image/auto-orient,1/quality,q_90/format,webp)
近读裘帕.拉希莉的长篇小说《低地》,被她跌宕起伏的情节、绮丽灵动的文字、巧妙叙事的技巧而体味到整部小说的精致动人。小说以印度托利冈吉和美国罗得岛为背景,讲述了美国印裔移民特拉家两个儿子,以及父辈、自我和子女的经历。哥哥苏巴什和弟弟乌达安出生在印度,苏巴什老成稳重,乌达安行不苟合。苏巴什赴美攻读博士学位,乌达安在家乡投身革命,这使兄弟俩有了截然不同的人生。
小说中重要的女性角色是弟弟乌达安的妻子高丽。高丽后来也是苏巴什的妻子。由于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和疏离,违背了世俗伦理关系。当丈夫乌达安被警察枪杀,给高丽带来了极大的心灵创伤。这时她的精神状态是紧缩的、内收的、封闭的,迷茫和无能为力的。她选择嫁给乌达安的哥哥苏巴什,并随他飞往异国他乡,生下前夫的孩子贝拉。这一举措突破了印度人的传统思维,是她寻找个体生存的意义所在。
而苏巴什呢,因为在赴美留学前就知道弟弟乌达安秘密投身于纳萨尔巴里运动,还曾受到乌达安邀请参加过加尔各答北部召开和商议的秘密会议,但是他后来选择了赴美留学。对于弟弟的惨死,他因没能及时劝阻而倍感内疚和自责。这一定程度上,来自他对高丽处境的怜悯和同情,决定娶她为妻。
在新建立的家庭中,高丽并没有认同作为妻子的角色,也未做呵护女儿的好母亲,看似美满的新家,背后却是千疮百孔。两人共同生活了十几年,乌达安的死仍旧困扰着高丽,挥之不去的阴影让她只好研习西方哲学课程,获得博士学位。在贝拉十二岁的那年,高丽思索着是继续在家庭中维系冷漠的亲情,还是勇敢出走、活出自己的人生?她最后选择了不辞而别,去加利福尼亚的一所大学任教。她的摆脱和逃离,无意中又一次颠覆了印度传统文化,造成了女儿的心理创伤,让这个艰难中建立的家庭四分五裂。
苏巴什是个勇于承担责任、直面创伤的男人,他独自承担抚养贝拉长大;作为乌达安的哥哥,在弟弟被枪杀之后也蒙受心理创伤,这体现在愧疚和自责所造成的“自我分裂”;而贝拉因为缺乏母爱,伤痛,秘密也传递到了她的心里。她在谎言中生活,承受着人生失去支点的空洞。在学校里,她落落寡欢,总是和其他同学保持一定的距离,即便苏巴什给她请来心理医生,她还是逃离了学校。她到处流浪,在农场和超市做工,从事各种公益活动;之后她未婚先孕,生了女儿梅格纳后,回到苏巴什身边。
面对贝拉的女儿时,苏巴什再也不想藏匿家中的谎言,鼓起勇气向贝拉袒露了她生父的秘密。这意外的消息颇让贝拉震惊,但她只得承受亲生父亲被枪杀的事实。想起母亲高丽的不辞而别,她将自己缺失的母爱弥补在女儿梅格纳身上;带着女儿梅格纳,她再一次逃离了这个家。
乌达安的死亡影响了整个家族成员,母亲比卓利失去了二儿子,苏巴什失去了弟弟,高丽失去了丈夫,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失去了亲生父亲;大家选择对此事闭口不谈,这种创伤带来的沉重打击,让家庭所有人都保持沉默并封闭自己的内心。为此,作者裘帕记录了创伤在隔代之间的传递,让从没有直接经历过创伤的个体,继承了死去已久的先人的创伤记忆。家族隐秘的创伤,在后代人的心灵中成为创伤的间接承受者,由此而产生心理分裂。
低地和罗德岛虽为印度和美国两地,却为一体,它们都充满着无法摆脱的伤痛和无可替代的回忆,如同高丽和苏巴什虽然身处异国,但记忆仍旧沉潜于低地中无法摆脱。因此家里人都企图逃离家乡、逃离悲痛,好在最终贝拉和高丽选择了回归,将几代人重新拉回到那个掩埋在荒草之中的家,如同水流向低地,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让他们在过程中,有了对谎言、疏离的终结;对责任、爱与自我的认知和回归,这才是明智对待所有经历的价值所在。
值得庆幸的是贝拉终于明白继父苏巴什的一片苦心,她和母亲最终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和解,更重要的是苏巴什找到了自己的爱人,晚年和美国女人走进了婚姻殿堂,这似乎是作者给苏巴什悲剧人生的一个补偿吧!
裘帕.拉希莉是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是继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后,又一位在英语世界获得广泛赞誉的印度裔英语作家,《低地》是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印度与美国,在这部小说中不仅包含着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内涵,更是两个异质空间包裹着关于个人生命的创痛、记忆与遗忘的哲思。
2025年3月19日修改于华盛顿特区
原载《中国日报》世界华人周刊版2025年7月1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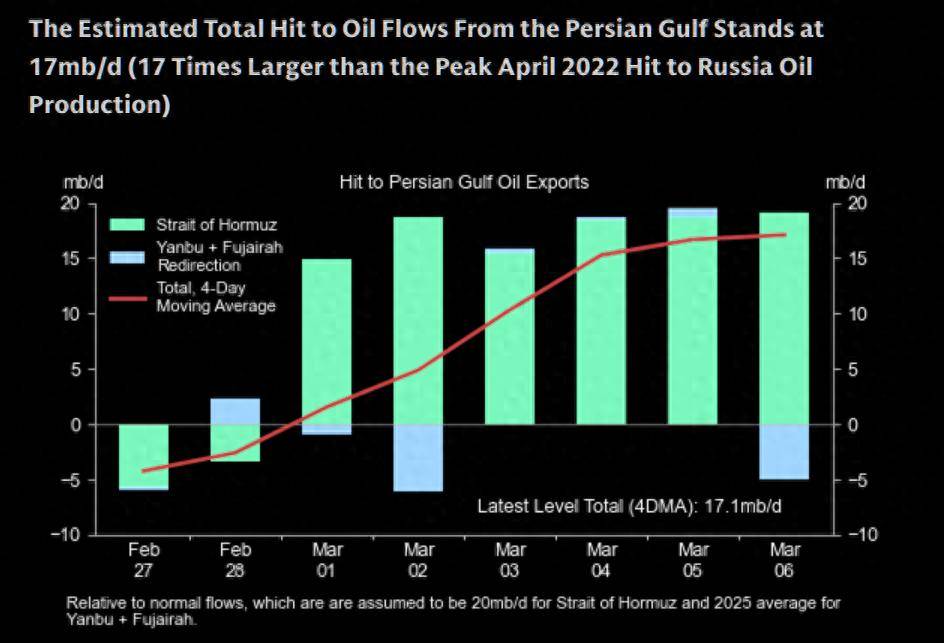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