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海西
![图片[1]-钓鱼-华闻时空](https://hwsk.oss-cn-shanghai.aliyuncs.com/2025/11/image-73.png?x-oss-process=image/auto-orient,1/quality,q_90/format,webp)
腊月初八,太公山庄的灯光暖得像是要把窗外的寒气都融化。
天黑了,周贵、正雄带着两位客人从楼上下来。命达、薛闽、东东等人都站了起来,跟随着他们,进了老榕包间。
大家坐下后,周贵就对每个人作了介绍。两位客人,一位是日本客人,东洋珠式会社首席代表尾本大力先生。一位是政府办公厅杨主任,因为办公厅正、副主任都姓杨,就称杨主任为大杨。
大杨刚从国外考察回来,今晚命达张罗着给他接风洗尘。包间里摆着一张红木圆桌,水晶杯在灯光下闪烁着细碎的光。
看到尾本比夏芳还高出半个头,东东对夏芳说,“‘一丈青’女士,来了一个‘丈二和尚’,比你还高。”夏芳嗔他一眼,东东看着她暗笑。
摆好酒菜,有的吃有的喝,大家轮着向大杨和尾本先生敬酒。
“你们真是幸福,吃香喝辣,逍遥自在,天天有鱼钓。”酒过三巡,大杨给尾本续酒,“我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陪领导去欧洲考察,那西餐实在是淡乎寡味。”
尾本先生西装笔挺地坐在主宾位,时不时用蹩脚的中文插话。
薛闽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衬衫领子有些发黄,正滔滔不绝地讲着他在欧洲访学的见闻。
“别班门弄斧了,你去的国家比主任多?”东东打断薛闽夸夸其谈,“主任周游列国,见多识广,谈一些西洋镜,让我们开开眼界。”
大杨说,“那些山啊水啊,虽然各有特色,但也不过如此。”
周贵说,“我也是,游山玩水没意思。去年在巴黎,整整七天我都在罗浮宫看。”
大杨说,“酸不酸,问你,卢浮宫最好的艺术品是什么?”周贵猜是维纳斯,薛闽猜是蒙娜丽莎。
大杨说,“周贵你白看了七天,都不是。卢浮宫最好的艺术品,就是卢浮宫。”一语既出,四坐皆惊。
薛闽秉着做学问的认真劲,说“愿闻其详。”
“贝聿明大师设计的卢浮宫入口处,玻璃金字塔,遭到不少非议。”大杨与命达碰杯,“但是你走进金字塔,透过玻璃屋顶,卢浮宫就像一座天堂,与在外面看,效果确实不一样。”
尾本只是闷头吃喝,偶尔露出听不懂的尴尬表情,夏芳为他翻译。
“主任真是讲到点子。学哲学的,理念就是不一样。”曹溪举杯自饮,“像贝聿明这样的大师,不但要有工程师的技术,更要有哲学的头脑。”
大杨说,“你们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是什么?”夏芳猜是金字塔,或者万里长城。
夏芳悄悄把白酒换成了矿泉水,被东东发现后娇嗔着罚了一杯。
“是城市一一人类最伟大的作品。”大杨用餐刀切一块牛肉,“上下几千年,纵横几百里,了不起。”
命达说,“以后去旅游,多看城市。”大杨说,“但看城市,也不过如此。”
尾本瞪大眼睛,夏芳受不了杨主任的高高在上,卖弄聪明,“那旅游,就没有东西看,还游个屁。”
大杨说,“有啊,看人! 旅行观光也要以人为本嘛。”
“是是是,以后出国,就天天去看人妖、天体浴场。”命达挺着啤酒肚,手腕上的金表随着他夹菜的动作一晃一晃。正雄笑着说,日本的“人体盛”还等着你。
“一位伟人说,人的品质是自然风物和社会风情的总和。”大杨喝了一口王八汤,“看风景不看人,太幼稚了,只是皮毛。”薛闽问伟人是谁?大杨并不回答,卖关子。
“各色人等皆有可看之处。”命达显出见多识广的神色,“我出国旅行,不照风景,都要找人妖、部落酋长、草裙舞女郎照相,那叫特色风情。”
柳眉举起高脚杯,向大杨敬酒。大杨问了她名字,“‘柳眉’好名字,‘芙蓉如面柳如眉’,杨贵妃啊。”命达说,刚刚聘她做售楼部主管,能力强,业绩很好。
大杨早就关注了她。黑色的旗袍衬得肌肤如雪,耳垂上的珍珠耳坠微微晃动。酒桌上男人们的目光,像飞蛾扑火般黏在她身上,她却始终保持着恰到好处的微笑,既不热络也不疏离。
有人过来敬酒,她端起酒杯浅浅抿了一口,鲜红的唇印留在杯沿。她说话时声音很轻,像羽毛拂过耳畔。虽然有点刻意,却总能让人不由自主地凑近倾听。她将长发拢到一侧,露出修长的颈部。
“杨柳本是一家人,‘春风杨柳万千条’嘛。”喝酒的命达,突然有了灵感。
柳眉与大杨对饮,“主任还挺平易近人的。”大杨说,“你这一说,我好象不是人了。”
薛闽也是嘴欠,抖机灵,“主任当然不是人——是‘猪人’”。大杨瞪他一眼,薛闽说,“失敬失敬。我罚酒!”
众人正为薛闽捏一把汗,不想大杨狠狠地表扬了他,“教授一语道破。女人喝酒变成男人,男人喝酒就变成‘猪人’了。”
大杨自我解嘲,大家松一口气。“按照弗洛依德的理论,”薛闽更加得意忘形,“人喝了酒,‘超我、自我’都管不了‘本我’,人都成了动物‘猪人’。”
“翘尾巴了不是?谈哲学,轮不到你。”大杨点了一根华子,“弗洛依德发现‘三我’,本我、自我、超我。其实人有‘四我’,如同唐僧师徒四人。唐僧是‘超我’、悟空是‘自我’、老猪是‘本我’。那沙僧嘛,就是‘非我’。”
薛闽语气谦逊地问,“什么是‘非我’?”
大杨说,“‘非我’,就是‘我不是我’,是人的奴性。”
薛闽说,“精辟!主任的‘四我’,是对弗氏‘三我’的扬弃。”
尾本日本话问夏芳,“他们都说了什么?”她回答,“我也听不懂。”
“不记的谁说过,”薛闽夹一块西蓝花,又不谦虚了,“国人自古以来,就只有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做不稳奴隶的时代——这就是‘非我’。”
大家高谈阔论,正雄与尾本“交头接耳”。柳眉举着酒杯,在席间穿梭。看看大家停下来,命达对柳眉说,“请主任跳舞。”
柳眉说,“就怕主任不给面子。”
“很不好意思。三步四步,我都不会。”大杨掐了只抽半根的华子,“单位里的人,都说我是‘不三不四’……有时我在想,很多民族都有歌舞,为什么汉族就没有民族舞蹈?这是不是跟以前女人裹脚有关?”
命达说,“嘿!这是伟大的发现,马上申请专利……”大杨说,“你这生意人,就知道钱钱钱,三句话不离本行。”
周贵去洗手,薛闽也跟着出来。周贵说,“你刚才也太大胆了,说主任是‘猪人’。”薛闽说,“官场上啊,你还是当局者迷。有时候,要刺领导一下。”
说来听听。
税务局的一个科长,想当处长,给局长送了两万元。后来,处长让别人当了。科长越想越气,就把局长的座车砸了一个洞。过了两个月,科长还真当了处长。
你这是胡说八道。
苍天在上,这是真事……税务局那么多人,大家都巴结局长。局长拿了科长的两万元钱,随便一扔,忘记了谁送的。但车窗被砸了,他就记住是谁干的……有时候,不在于你干了什么事,而在于如何让领导注意你。
这一套比“厚黑学”还黑。这就对了,这叫“黑黑学”,黑吃黑嘛。两人相视而笑,心领神会,一起回到酒席上。
尾本举杯站起来,”叽哩瓜啦”一通。正雄说,“尾本先生说有事,先走,敬大家一杯”。尾本喝了酒,鞠躬九十度后离开酒席。
周贵说,“我们要成立‘钓友协会’,特请杨主任当名誉会长,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大家鼓掌表示赞同。
夏芳特别会来事,总能在大杨酒杯见底时恰到好处地添上。她的笑声像银铃,眼角的亮片在灯光下一闪一闪。
“哈,社会上很多部门,请我当顾问,我都推了。”大杨举杯摇晃,抿了一口酒,“这‘钓友协会’的名誉会长,我还真愿意当。我喜欢钓鱼,也定钓鱼杂志,对垂钓之乐很有兴趣。”
“我建议,主任当了名誉会长,周贵就当会长。”夏芳也举起杯来,“再设几个部,联络部、开发部、宣传部、计划部,等等。这些爷们,都弄个‘部主任’当当。”
薛闽说,“既有大主任,又有小主任,我们都成了‘猪人’。”
大家听了,一阵哈哈大笑。
大杨有要紧事,也先走一步,向大家告别。大家离席,出门相送。
周贵开车停在门口。正雄把一个大箱子,放在后车厢,“这是尾本先生送给你的渔具。”大杨说,“不是有一套了嘛。”
正雄说,这套渔具,科技含量更高。有确认垂钓位置的GPS卫星定位系统,跟踪水下鱼群回声测量器,无线电传导的电子咬钩显示器。还有野外帐篷,微型渔船,碳素钎维钓线,合成铝钓竿,是日本最先进的渔具。
大杨说,“这么好,代我谢了!”
他与大家握手道别上车,周贵将车徐徐开出。
“你竞聘上岗的事,我不能跟老板直接提,”大杨斜靠在后排右座,“那样可能有反作用,弄巧成拙。最好是想个办法,让老板先认识你。”周贵想,大杨怎么说的跟薛闽一样。
老板最近经常说“观念要更新,方法要创新”,其实也就是哲学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观念更新谁都知道,老板的重点在强调方法创新。你写一篇谈方法创新的文章,我拿到《弄潮》上去发表。《弄潮》是老板每期必看的机关刊物。对了他的口味,他就记住你了,然后我再找机会推荐你。
周贵说,“这不是‘四人帮’的一套吗?”
“周贵同志,问题不在于使用什么手段,而在于谁在使用手段,”大杨摇开车窗,“同样一件事,可以说是‘阴谋’,也可以说是‘策略’,那就看谁在做。”
当年啊,有一个举人,找到李莲英,让他向老佛爷推荐。小李子问他有何特长,举人说会写一笔好字,小李子就让他在一把扇子上题字。夏天,小李子陪老佛爷在颐和园散步,拿着那把扇子,为她扇风。老佛爷看到扇子上的字,说“好字。”他说,老佛爷要是喜欢,扇子就留着。老佛爷就记住了这个举人。后来有了官缺,举人就补上去。你说小李子这招是阴谋还是策略?
冬夜的城市像一头沉睡的巨兽,路灯是它半睁半闭的眼睛。大杨主任用纸巾擦拭挡风玻璃上凝结的雾气,脸贴近车窗。车流排成看不到尽头的长龙,红色的刹车灯连成一片,如同一串被冻住的糖葫芦。
收音机里放着老歌,周贵调低了音量,车窗外传来此起彼伏的喇叭声,有人等得不耐烦了。
前车的后备箱上贴着”新手驾驶”的贴纸,司机不停地看后视镜,手指在方向盘上敲打。
人行道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个晚自习下课的男生,背着书包飞奔而过,校服外面只套了件薄外套,围巾在身后飘起。路口执勤的交警看了他一眼,又继续指挥着堵塞的车流。
望着街上车水马龙,大杨说,“众生忙忙碌碌,也不知为了什么。”
周贵说,“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去。”
大杨说,“女人嘛,古人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男人嘛,无非就是为了,‘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红灯终于开始倒计时。周贵松开手刹,手把方向盘。绿灯亮起的瞬间,车流缓缓移动,像解冻的河流。城市依然灯火通明,周贵的车汇入其中,成为冬夜里一个移动的光点。
把主任送到机关大院,周贵回到家,洗了澡躺在床上,胡乱翻看一本旅游杂志……
老父亲穿着那件旧棉袄,
站在老家的枣树下,
手里还捏着半截旱烟。
“孩子啊,”父亲的声音,
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咱农家孩子,
最要紧的就是本分。”
烟头的火星忽明忽暗,
映着老人布满皱纹的脸,
“不该拿的别伸手,
不该要的别动心。”
周贵想要辩解,却发不出声音。
父亲叹了口气,烟灰簌簌落下:
“人这一辈子,该是你的跑不掉,
不是你的强求不来。”
窗外传来一声猫叫,周贵猛地惊醒,后背已经湿了一片。月光如水,依旧冷冷地照着,墙上挂着的全家福里,依稀可见老父亲的模糊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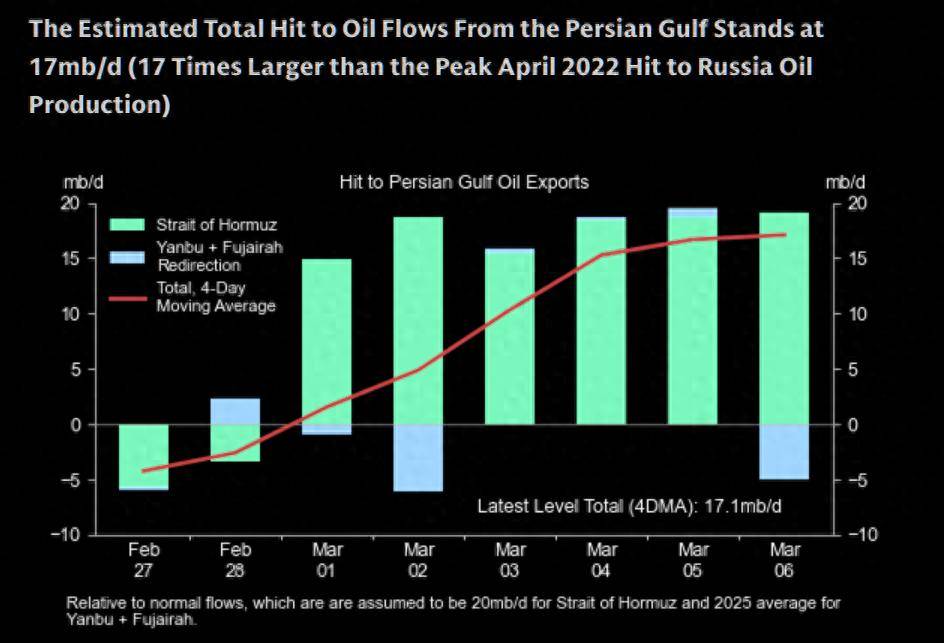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