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难忘——缅怀邓师恭三先生
张广达
编者按:本文完稿于1998年5月20日,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00—207页。
张广达先生
张广达先生部分著作
1998年元月11日,北大历史系发来电子信件,告知邓师去世的消息。此前,我已知道邓师不幸身罹绝症,卧病医院数月。邓师年届91岁,回生乏术,已在不免。然而,预料中的事情一旦成为现实,我依然受到巨大的震撼,沉浸在悲痛中不能自已。
稍稍平静后,我给邓小南师妹发回一封短短的吊唁信。发完后我怔怔地守在电脑屏幕前:邓师走了,生顺死变,又是一场无可奈何的永别。我认识邓师是在1952年暑假之后。45年来,我身受邓师的知遇之恩,难以为报。而最近十年我羁身海外,不得亲聆教诲,更未在邓师临终前略尽心意,心中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1952年夏,教育部依照苏联的模式,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调整。我原在燕大历史系读书,院系调整后成为新北大历史系的首届毕业班学生。1953年毕业留校,任世界古代史胡钟达先生的助教。当时,胡先生住中关园一公寓,和邓师住上下楼。我经常到胡先生家,不时碰到邓师。胡先生的母亲为了清凉去火,使用沏过又晾干的茶叶装枕头,邓师经常亲自托钵把晾干的茶叶送下楼来。
在当时,邓先生属于“老教师”之列。所谓“老教师”,除了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专治欧洲中世纪史的孔繁霱先生年逾60以外,其余教授53年时都不老,向达先生52岁,杨人楩先生49岁,周一良先生40岁。当时历史系很多名教授济济一堂,皆一时之选,真可谓郁郁乎文哉。那时我23岁,学无根底,不谙世事,但出于我的价值取向,我对这些老教授自有一种亲和力。那时邓师年在四十五六岁之间,身体健康,神采奕奕,对我非常亲切,蔼然有长者之风。有一次我与胡先生告辞后,和邓师一起走出胡先生家,邓师主动邀我到楼上他家坐一坐,把他刚刚收到的新刊《岳飞传》(该书初版)签上名送给了我。
在我第一次去邓师家,邓师就谈到,治学要打好根底,“根深才能叶茂”,至今铭记不忘。邓师还谈到,研究历史,不妨写些关键人物的传记,这是很好的入门途径。我注意到,在宋史研究中,邓师不仅下大工夫研究制度,如宋代职官,也认真研究宋代几位关键的人物,通过个案深刻剖析宋代的历史。他一再增订的王安石、岳飞、辛弃疾、陈亮等人的传记,从政治、军事、文化、事功等多方面加深了宋史研究的深度。在海外,刘子健先生之研究欧阳修等,也是同样的治学路数。
但那时我还不知治学为何物,费了不少时间翻译苏联《古史通报》、《历史问题》等杂志上的佶屈聱牙的文章,充分表现出我分不清什么是有长远价值的学术,什么只是一时的热闹。自从与邓师接触以来,我开始意识到中国人研究世界史不能脱离中国史。邓师的博学多闻和妙趣横生的谈话对我极具吸引力,他对我讲过在北大读书时,与张政烺先生同上姚士鳌(从吾)先生课时的轶闻;对我讲过当年北大教员可以随时进入校长办公室而与胡适谈话,平时也总有不少人在这里高谈阔论;讲过郑天挺先生任北大总务长时的干练清正等。
逐渐地,邓师成了历史系重业务、轻政治的典型。他在讲课中曾向学生提出过,地理、职官、年代、目录是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为此多次受到会上会下的点名批评,邓师被攻讦的最大理由是,“单单丢掉了最根本的一把钥匙——马列主义”。其实,这并不符合邓师的本意,邓师是当时历史系发表论文最多的先生之一,他常常为进行对比研究,为开阔思路而求助于理论学习,常常重复当时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先生的话:有了许多制钱,还要有把这些制钱贯穿起来的钱串子(指理论)。1988年,邓师为日本宋史学界发起的《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同朋舍,1989年)写了一篇序言,其中谈到:“认真说来,仅仅借助于我所列举的四把钥匙,以及前代学者所提的文字、训诂等,作为现代史学工作者的研究工具,也还是远远不够的。例如考古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心理学等,无不与历史科学的研究有极其密切的关联。在这些学科方面的造诣之深与浅,知识面之广与狭,对于一个史学家的论著质量之高与低,精到与粗浅,关系也极要切。”由此可见邓师前后一致的治学观。今天,已经不是在举办白专道路展览会上为邓师的“四把钥匙”单辟专栏的时代了,邓师的教导是正确的,学历史的人,既要学理论和尽可能多掌握治史的工具,也要像他那样开拓视野与胸襟,与时俱进。
一九八四年十月摄于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首届国际宋史研讨会期间。一排左四为刘子健先生,左五为邓广铭先生。
邓师过去与胡适、傅斯年有较深的共事关系。在批判俞平伯、胡适的运动之后,他仍然表达不合时宜的学术见地,当然易于被人抓住辫子。难得的是他表里如一,不管他人态度如何而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看法。圣人周公尚不求备于一人,谁也不能要求他人完美无缺。邓师令人尊重的地方在于他性格鲜明,不因时因势而改变自己的主张。在运动频仍、批判不断的日子里,邓师的想法有时不免天真。例如,1956年规划向科学进军的时候,执著的事业心使邓师很兴奋,他真的认为知识分子的春天来到了。听到对专家学者即将有一番优越的待遇,邓师也很感兴趣。我当时正给一位在历史系教苏联史的苏联专家当课堂翻译,邓师便向我打听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制度,对苏联院士享有的某些待遇大为赞赏,希望中国的专家也能像苏联的专家那样受重视。邓师尤其赞赏苏联政府给院士住宅门口镶嵌上亮晶晶的、写上姓名、住址、职务的大铜牌。邓师攒了些稿费,又听到了高级知识分子可以享受某些特殊待遇的传闻,他甚至于想用稿费给自己买辆汽车。在当时,他老先生可谓异想天开了,但这就是邓师。
1957年6月8日,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前此,我因狂妄无知,说了一些被认为“违反六项政治标准”的言论,受到若干场揭发批判,于翌年(1958年)2月的反右补课中被“补划”为右派,又于1959年十年大庆前夕被摘掉右派帽子,成为“摘帽右派”。在人人怕犯政治错误的紧张氛围中,谁都知道“右是政治立场问题,左是思想方法问题”。所以,无论对“戴帽右派”,还是对“摘帽右派”,都是以保持距离为明智。为了不给别人带来麻烦,我没事绝不接触任何人,遇见熟人,能绕道走就绕道走,能假装看不见就假装看不见。令我惊异的是,邓师对我的态度不改先前。我在下乡劳动或下放锻炼中偶然回校,邓师碰到我,总是以长者的关怀跟我说几句话,而在这几句话中传达着更多的言外之意,令我在人间冷暖对比中,对邓师给予绝境中的青年人的关怀刻骨铭心,没齿难忘。
摄于八十年代初,左二为邓广铭先生,右二为张广达先生。
就在这时,我耳闻邓师对别人讲:张广达是个人才,应该给他安排工作,这样既利于他的改造,也让他发挥一些作用。此事已过去近四十年了,任何时候想起来,我都感动不已。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饥荒遍及全国而强调劳逸结合,政治气候相对缓和。我向系领导表示愿意从世界史转向中西交通史,邓师听说后,当即表示支持。我后来终于从世界史转向中国史,完全是邓师支持的结果。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对右派的任何关照都可以在适当时刻上纲到丧失政治立场的高度,何况邓师有过与胡适、傅斯年的共事关系,这本身就是政治辫子,可被罗织罪状,招致灾祸。邓师为了爱惜年轻人而忽略了自己可能遭受的连累,这种无畏的襟怀令我永远敬重。邓师不仅对我,对其他与我情况相似的年轻人也深加爱惜。有一位53年入学的女学生戴静华,57年被划右,邓师对此非常惋惜,说:“可惜这个人才。”邓师似乎为此而受到过批判,被迫做了重业务短政治、重才不重德的检讨。邓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明知对他看重的青年人的热忱爱护可能为他招致麻烦,但他置之度外。在艰难困顿中,我既从他那里得到了师辈的温暖,也从他那里学到了怎样做人。我今天所以也能坚持自己的某些信念,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受邓师人格的感召。人活着就应该像邓师那样,如果是正确的,就应当不计个人得失而予以坚持,不应当随风摇摆。
《流水何曾洗是非——北大“牛棚”一角》,北京大学前副校长、历史系教员郝斌著,作者于书中回忆了从1966年文革爆发至1969年夏30个月中的经历。
1969年11月,北大教职工下放江西南昌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这里原是一处劳改农场,靠在枯水季节造堤围湖,与鄱阳湖底争地而成的圩田。由于土地本是湖底淤泥,所以干旱时坚硬如砥,雨天一下子变成黏稠的泥塘。遇上连雨天,泥深逾尺。人走在这种胶泥塘中举步维艰,即使穿着统长及膝的胶靴,深深的胶泥也把胶靴牢牢地吸住,往往拔出来的是脚而不是胶靴。就在这样一片土地上,北大数千名教职工受命建立干校,走“五七道路”。干校实行军事编制,由军、工宣队领导。邓师和我被编入八连的后勤排,邓师放鸭子,我在蔬菜班种菜,师生情谊走向更深厚的一步。那时邓师已年过花甲,头戴草帽,脚穿胶鞋,挽着裤腿,手里拿一根细长的竹竿,在暑气蒸人的田野上放鸭子,条件极其艰苦。像他这样的老教授在全干校也没有几人,可是邓师秉持素有的开朗乐观,能吃能睡,不改本色。开饭时,邓师拿着一只不小的搪瓷饭盆和大家一起排队打饭,吃满满的一碗,有时还加上些。睡觉时和大家挤在大统铺上,倒头便着。一段时间内,我和他并排挨在一起。我的工作主要是从厕所淘粪,把粪挑到菜地的粪坑里“沤肥”(发酵)。当我挑着粪担来回时,常和邓师聊几句。师生关系越来越亲密,有时甚至开开玩笑。鲤鱼洲夏天奇热,冬天奇冷,冬天的条件更加艰苦。邓师和我以及绝大部分下放教工都得了尿急尿频症。这些,邓师和我都一起熬过来了。
1978年,邓师任历史系主任,当时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邓师提出“实事求是”四字作为他的办学方针。他对“文革”中历史系人才凋零的惨相有切肤之痛,不顾年事已高和脑血管硬化而致力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他怀着十分焦急的心情,网罗全北京市的优秀教师为历史系学生开课,并提出大、小通史方案。自历史系主任卸任后,他又着手筹办“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着眼于出人才、出成果,这是老先生非常有战略眼光的一着。从邀集人发起,到“中心”逐步成形,全由邓师亲自擘划操持。中心建成以来,在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人才方面成绩非常突出。今天北大历史系中古史后继有人,凝结着邓师的心血。说来惭愧之至,在“中心”筹建过程中,我未能为邓师分劳,迨“中心”建成后,邓师却让我忝任副主任。“中心”的很多事情我并没有做好,辜负了邓师的厚望。
我生平第一次正式讲课是在1978年,担任“中国通史”后半段,这是邓师亲自安排的。1981—1982年我在荷兰莱顿汉学院访问,其间到了英、法。回国后,邓师亲为我主持了一次全系师生出席的讲演会,让我报告国外见闻。我还记得,邓师也为我主持过学术报告会,我当时的讲题是“碎叶城今地考”。所有这些安排,都渗透着邓师提携我的苦心。他说:“过去京城名角都需要人捧场,学人的成长也一样。”邓师对他垂青的学生,非常重视为之创造成长的条件。有一次我对马雍学长谈起邓师,马雍学长立刻说:“邓先生是我的恩师。”
随着改革开放,回忆和记述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的书籍、文章多了起来。读了这些著述,我方才醒悟,邓师正是本着陈寅恪为他的《宋史职官志考正》作序的精神提携后进,正是发扬胡、傅秉公处事的精神培养学子。我感到邓师身上有胡、傅两位先生的作风的影子,包括不怕开罪人的作风。
1987年春,我和邓师同受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邀请,大致同时到了日本。从东京到京都,我亲眼看到了日本老、中、青不同年龄段的宋史学者对他的崇敬。1988年,日本宋史学界筹划出版刘子健先生祝寿文集,序言就是请邓师写的,序言前后印上邓师手迹,然后附上英、日译文,充分体现了国际学界对邓师的敬重。我为邓师为中国史学争得的荣誉感到由衷的骄傲。
1989年夏我来到国外,在巴黎一呆八年,来美又将两年。我一再拂逆邓师促我返校的心意。然而,邓师并未对我生气。对我的关心爱护一如既往,有增无已。迨知邓师入院查出绝症,我心知此去凶多吉少,数月来惴惴不安。获悉邓师辞世的噩耗,我终于面临了无情的现实:每每于我艰难竭蹶时刻而雪中送炭、向我伸出温暖之手的恩师永远离开了我。
张广达先生,图中旅馆是他第一次出国在巴黎所住的地方。
我生也驽钝,学无所成。邓师生前,每次得知我有点滴成就而由衷喜悦,但也为我的笔下枯涩老写不出大块文章或专著而内心起急。他通过各种途径予我以督促,希望我早点儿拿出著述。作为学生,未副恩师厚望,我十分惭愧。但可告慰老师的是,我一天也没有荒废学业,只是由于根不深,没有做到老师要求的叶茂。十年来,在海外授课之同时,补了补中外基本典籍,略略考察了欧陆和美国的治学路数。我行年六十有八,余生无几,唯有以邓师的期待督责自己,尽心致力于撰述,以报邓师的恩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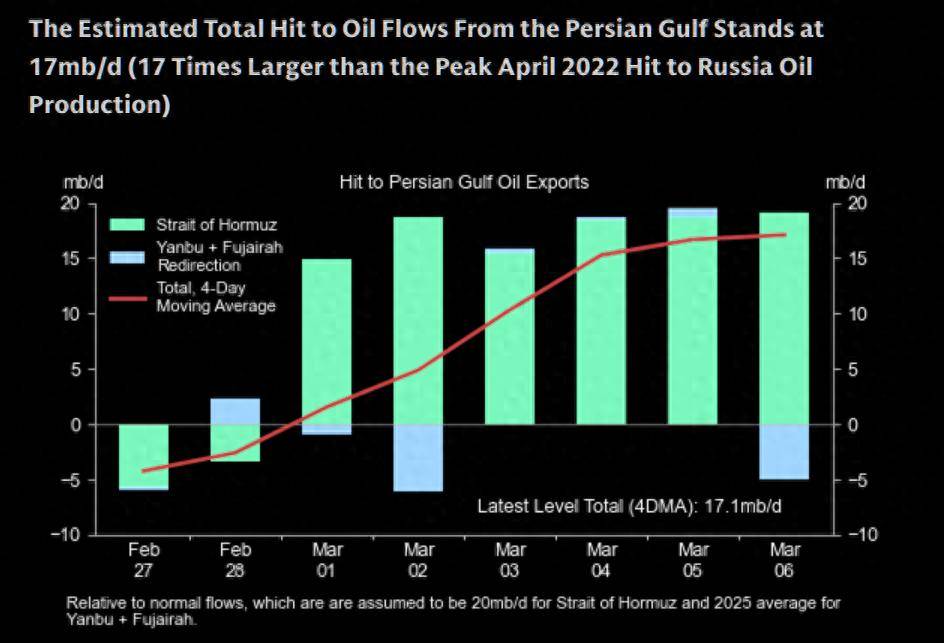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