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其
杨皓更像一个商业社会的理性适应者,或可称其为恪守资本主义伦理时代的诗人。关于日常的诗性早已构成一个从寒山到施耐德的传统,但从一个诗性丧失的时代的境遇,仍能迸发日常藏锋的诗机,杨皓的诗歌却给人意外之新。
虽有内心澎拜的抒怀诗,但杨皓的大部分且杰出的诗作,则是于平淡庸常的日常性中叠出诗机。这些诗作往往是直白的措辞,在反诗意的时代语境中却诗意迸发。因为微妙而无奇中意兴闪现,几乎难以被称为传统意义上的诗意,而是一种程式化的世界架构的无趣缝隙中冒出的诗机。
杨皓的诗展现为一种日常性中具体处境的诗机,与诗歌的宏大抒怀或语言本身的遣词实验的视角不同,他的诗歌回到了一种具体事件和日常性的处境,置身并依傍这一具体而日常的处境,才能于当下的切身感识,迸发超越眼下庸常的意识与怀想,有些是广远的,有些则是类似微动的禅机。
他的诗歌因而大体上归于纪事和纪游两类。前一类从琐事到波及全球的疫情,比如为疫情而作的《最后的忏悔(写在武汉封城之前)》、《在茉莉小丘龟息的一年》、《柯伟德拾玖Covid 19》、《中国仍在经受那致命的最后一击》,以及关于黑命运动的《乔治•弗洛伊德》。另外,专为艺术作品和艺术展览创作了不少具体的题事诗,比如《达摩未能渡过长江(为石冲个展而作)》、《致我们的母亲大蜘蛛(为龙美术馆布尔乔亚大展而作的诗歌)》、《退步——为陈丹青的同名油画个展<退步>而作》。
关于艺术交集的诗歌,并非在于赞赏或回味艺术的审美享受和至高的境界,而是玩味艺术所处的时代乱局及庸常之扰。比如《在草场地》,写去北京大山子的一个著名的艺术区,却宛如穿越一个无趣的城乡结合部,去一个充满审美期待的画展,但却遭遇一个前路徊惶的死胡同般的帝都空间:
我在寻问每一个
路过的人
没有人知道我要找的
确切方位
所有行走的人
大都一脸迷茫
他是去看湖北友人石冲的画展,却陷入了一个时代的迷阵:
在草场地
我是一个迷路者
我能找到成坏的肉身
但找不到北
诗中所出现的空间情景谈何诗意,但当杨皓闯入这个诗意荡无的日常处境,他自己就是诗机。为了在大量的庸常语境中寻求出口,诗中设置了大量的假设性的古往视角,比如《达摩未能渡过长江(为石冲个展而作)》,假设了一个达摩的叙事视角:
我看见达摩在既渡未渡之岸的
焦灼
他在寻找一只
未渡之舟
而石冲一直没有
远离现场
在达摩过河的渡口,杨皓的耳旁仿佛不断飘来诗的声音:
我听见腐败在歌唱
听见杂质和凝固的乳胶
在与那些胴体
的合欢之歌
我听见空气和水的私语
看见欣慰中的年轻人
和被晒干的
一堆死鱼
以这样一个假设性的古往的历史视角,杨皓创作了一种诗歌类型,比如《陪同孙中山先生回湖广会馆》、《我持楚国的护照而来》、《昨天我陪李白在长岛过夜》。这一类诗歌的叙事方式,不仅以一个近代或古人的观照性的比较视角,又是一种文人传统的纪游诗体,即游历了某地,置身具体的情景的感时伤怀。杨皓的纪游诗延续了一种历景伤怀的文人玩味,但情景时空置换了一轮时代新情志。比如游历孙中山下榻过的虎坊桥的湖广会馆,周边多了共享单车、郭德纲的德云社、私房楚菜馆。一切物是人非,此为诗之常情。但杨皓的诗总能在黯然收场之际,话锋由陋巷窄口陡出全景开合的机锋:
革命确实尚未成功
同志已分散各处
许多人成了地产商人
国家仍在分裂中
这不仅在于引入一种历史的古往现场,过去的当下场所由于历时被时间化,但这一时间化的历史场所却再一次被双重时间的定义化,即同一空间被两次时间化定义,空间情景在两次的时间定义中被赋义为一种意义再造。
针对具体事件的纪事诗及游历特定地点的纪游诗,成为杨皓关于日常性中藏锋机出的一种体裁,在意淡寡味的当下现场中转捩意外之奇。在此,杨皓的诗经常是一种禅机和诗机的交叠或互渗,这不仅在于他钻研禅宗及从寒山至施耐德的传统,后者将禅诗发展为一种现代的日常白话。从寒山到施耐德的自然禅的核心在于体味日常的当下寡味灵动,但杨皓显然志不在当下冲淡之超脱的涵养,而在于在日常之中找到一个深闳思怀的破口,将人文的诗怀以历史、文本及批判视角植入某一日常破隙,从而将日常意识从某一具体事件、地点拉向一个当下之外的历史和人文时空。
诗机的破口就成为整体的日常叙事中的一个核心所在,通过某一个日常的叙事切口,植入一个日常之外的超日常联想,这一切口即诗机的破口。比如《七月一日凌晨四点陪女儿赴天安门看升旗典礼》,一开始即“沿着《金刚经》指引的道路/我们如约抵达天安门”,随即插入一个古往的身份:
我来自唐朝
是寒山子庞居士的
转世兄弟
诗歌最终在广场脚步徐行的缺口,诗机陡然而出,将封闭的具体时空引向当下现场之外的意识涌动和超现实的景象:
沿着《金刚经》指引的道路
我们前行
在太阳升起之前
踽行在指定的地点
露珠打湿了
我的双脚
倏然间,我发现
脚下的水泥地上
长出了
青草
诗机在日常当下的破口而出,又是一种禅机化的思想视角。有时是佛教的,有时是现代意识形态的。佛禅是杨皓的诗歌经常出现的一个思绪视角,如《卢舍那大佛》、《我在禅宗的山上》,偏向于一种佛说的思辨。这定义了诗歌与佛思的一种关系,即佛说作为一种看待当下的视角,并不在于佛禅自身的析理或禅境的回味,而是对纷乱、污秽及正邪的一种日常思辨。
在杨皓的诗中,佛禅作为一种观看的视角,这一视角代表着一种诗机和思机的合一,或一种破除日常滞闭的破口。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思辨的诗机化,同时是一种诗机的思辨化,二者是同一的。杨皓显然并不试图将当下造就为一种自足驻留之地,在其笔下,当下恰是一种庸常、卑陋、纷扰的非自足之地,需要从这一非诗性的封闭日常世界破开一个当下之外的意识世界的切口,这一意识世界无论是历史的,抑或意识形态的。
对于杨皓而言,一个身体在当下的日常事件或具体空间之中,从主体到周遭划开一个破口,就此植入一个思想和历史视野,即便这一视野是佛禅的。它是一种入世的观照,并以思辨的日常切口的植入,激发出一种感怀的超越日常的诗机。它表现为一种历史地点、文本以及佛说的联想植入,使得具体而闭合的日常世界,通过一个意念破口与超验意识和历史世界贯通,达到对当下意识的滞留及其自足化的一个超越,相比于从寒山到施耐德对禅的自足性驻守,在心理上杨皓显然更为积极。
具体的地点是当下世界与超验世界的一个接口。杨皓的诗中,日常的具体空间是一个闭合且纷杂的非诗意甚至无望的世界,当这一世界入诗,唯有通过一个与超验世界连接的接口,为其灌注诗怀及思辨,庸常的当下世界才会在诗中复活,由于另一世界的魂气注入,沉闷的日常被破开了通向另一个意义时空的口子。
历史地点成为两个世界的一个经常破口,或者在布鲁塞尔(《布鲁塞尔广场飞出的天鹅》),或在瓦拉纳西(《在瓦拉纳西》),或在京都(《京都枯山水印象》),或在拉斯维加斯(《登机牌21 :我要把我的一小撮骸骨留在拉斯维加斯》),或在太阳城(《在太阳城》)。因而纪游体被发展为一个缅怀性的日常思辨,并一定程度吸收了禅诗对当下之境的玩味。
地点是纪游体及禅诗的叙事依托,通过地点这一破口,接上另一个超验的世界,使其成为一个“现世/超验”的双体结构。在关于地点的日常性和具体性的超越中,历史成为一个超验世界,或许这一定义是中国式的,因为地点的历史化之后,过去情景的现实性被转换为一个超验的意义世界。它作为一个考量当下日常的甚至被切断未来性的一个标尺性的未来视角。
这一视角的绝佳例子是《布鲁塞尔广场飞出的天鹅》,布鲁塞尔作为共产国际成立以及《共产党宣言》发布的地方,在欧洲进入一个高级庸常的福利社会之时,一个破口出现了,杨皓就坐在这个破口上,他坐在马克思曾坐过的圆桌旁,此时,一个红天鹅彷佛从170年前的世界通过这个破口飞临当下,于是两个时空穿越的“诗/思”突然而至:
170多年过去了
天鹅并没有飞出
它的因果沼泽
追求幸福的路途
是如此漫长
它是如此真实
又似乎遥不可及
天鹅一直在飞翔
但束缚它的死结
一直没有解开
这样的轮回
还将持续
《京都枯山水印象》切入于一种美学的诗机,着重中国的南画山水与日本美学的“苍劲悲寂,而又幽玄枯淡”的重叠关系。想象性的诗机在一个叫龙安寺的石庭:
我幻化成那白沙间的
奇石
静听那枯海的
涛声
那尘世中汪洋肆恣的激情呢
痴爱与贪嗔
富贵与荣华都没有
从时光的沙漏中
逃逸
于是呈现出这一片
空寂的沙景
这是一段难得不带批判视角的山水畅想,对中日美学的重叠又分殊的把握深得三昧。禅寺的日式园林及空间意境,与禅诗的空淡意蕴的内在关联,使诗歌在庭院空间的层次,在中日两个山水时空的穿透中,回归了一种纯粹的诗机。
在纪游的地点之外,文本的联想成为另一个诗歌的破口。比如《马拉之死》、《巨流河啊,巨流河——读齐邦媛先生传记<巨流河>》,前者是一个置身布鲁塞尔的跨地点联想,这幅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大卫的杰作展示于布鲁塞尔的博物馆,这一画作成为革命思辨的一个破口:
血液从马拉的胸口
汩汩流出
流的好慢
已经流了226年
这一破口就在那幅画中马拉的胸部流血的伤口,这一“血流了226年”的叙事,使一个画面的伤口,成为一个关于革命的历史思辨,具有了穿越时空的现实性。诗的附注别有意味的成为正诗的一部分,马拉以革命名义的意识形态恐怖的省思,此时写作呼应了在另一个地点悉尼正火光冲天。
《巨流河》作为一个文本的地点,意指一个叙事性的象征。在这首诗中,“巨流河”就如马拉被拉长成一种历史失血,它变成一种文本空间的历史化,即一条悲剧性的不停流的历史之河,并且被看作不可渡过的宿命性彼岸:
然后我们终究
渡不过的巨流河啊
那伟大的虚空
将席卷我们
我们只能随波逐流
宿命和定数
从河流的那一边
把我们卷向那未知的
彼岸
作为隐喻性叙事的历史化,“巨流河”作为一种抒怀的诗机,因为宿命的悲观主义,诗机转化为一种思辨性的思机,但思辨中仍传递着诗兴磅礴的语言奔流感。
宗教的空间象征成为更为抽象的“诗/思”同构交织的一种价值观机锋。比如《我在禅宗的山上》一诗是作为新冠疫情的纪事背景,但在时事应急状况的叙事之后,却收场于一个象征性的景象:
人类不是越来越聪明
而是越来越愚蠢了
我在禅宗的山上
手里握着一块
冰冷的白石!
另一首诗《伊甸之东》是关于《圣经》的一个神话地点,交织着诺言、谎话、冲动、救赎以及乐园的荒芜等想象性的意象。但这并不是一种宗教畅想,而是在一个将神意之地历史化的日常思辨:
谎言说过了一千遍之后
还得再说一千遍
但思辨在这一神地的荒园化的意象,使得思辨变为一种诗意的感性抒怀,并呈现一种语言化的诗性形式:
环顾周围
四极八荒
那白色的岩石
仍屹立在山巅
歌声从岩缝里流出
古老而委屈
我领会了这一切
安慰着
这园内的大风
场所及其事件发生的日常世界,这一事件的具体的现实性如何超越,这是诗歌的如何超越日常经验的一个基础问题。诗歌的每次革命都要从语言修辞和诗性叙事的已有模式,回到这一当下的日常经验再出发,尽管这一方式也是一种传统,即从禅诗到垮掉一代自然禅的白话诗。
日常经验都是个体完成于某一具体的时间和场所,关键在它如何构建一个想象性的叙事,可以由场所的当下性及其闭合的结构,引入一个诗性的意义世界。在杨皓的视野中,诗歌是一个如何破开日常的封闭世界的场所经验的问题,即在日常世界中寻到一个当下的破口,并由这一破口溢泄出日常藏锋的诗机。
从这个叙事方式上,杨皓的诗在从寒山到施耐德的禅诗现代性这一脉络上,捕捉到了一种变革契机,它不在于语言自身的修辞,而是在一个日常经验世界与历史化的超验世界之间构建了一种对接结构及其想象性的转换。
2021年3月8日写于Bron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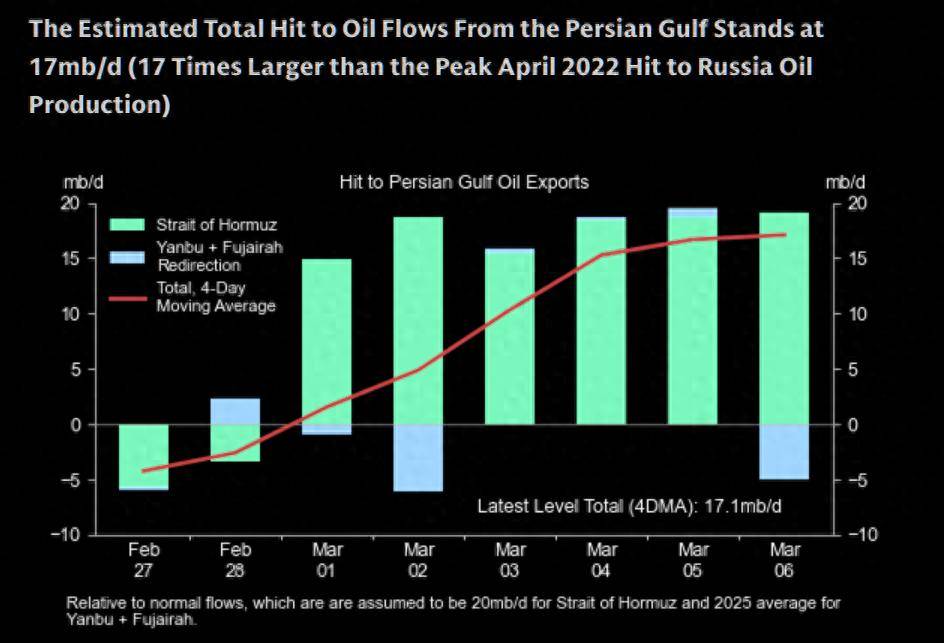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