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1]-文学路上的杂食者-华闻时空](https://hwsk.oss-cn-shanghai.aliyuncs.com/2026/01/image-101.png?x-oss-process=image/auto-orient,1/quality,q_90/format,webp)
读李利君小小说
杨晓敏
李利君在《小小说的九十年代后》中,展开多重视域的观察与思考。他从容解构小小说独特的美学质地,系统剖析诸多作家的创作得失,并透过现象,敏锐觉察到小小说所承载的文化经营意义——尤其是读者、作者、编者与运营者之间形成的良性互动。这一观察深具眼光。唯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土壤中,才可能孕育如此健康、促进社会平衡的文化形态。李利君融合了忠实读者、业余作者、评论者乃至文化产业观察者的多重身份。他自称“小小说的杂食主义者”,倒是十分贴切的自况。
评论文章时,李利君总是褒扬多于指摘,多予肯定、多赠鼓励。这般和风细雨的评点,落入写作者心田,仿佛早春悄然渗入冻土的暖流。人生与写作途中,谁都渴望获得外界的认可——有时哪怕只是一句话、一道目光,也能激荡出意想不到的感动与力量。比起那些需以“红包”换来的敷衍文字,这些常被主流视野忽略的小小说作者,能获得李利君毫无功利心的真诚关注,这些作品无疑是炎夏里的清风、沙漠中的泉音。据我所知,不少小小说作家视他为真正的知音。
他的不凡,还体现在将目光投向小小说的推动者——刊物与编辑群体。文化产业的概念近年来才受到广泛关注,而文化产品如何在保持品质的同时赢得市场、形成产业链,仍是各方持续探索的课题。李利君从小小说现象中,敏锐捕捉到其潜在的市场价值。他认为,郑州《百花园》《小小说选刊》杂志社堪称文化产业领域的“早行人”,它不仅是出版者与经营者,更似小小说的“传教士”,长期通过征文、笔会、评奖、编书等活动培育生态,精心设置“读者星空”“倡导者说”“编辑手记”等栏目,构建起作者、读者与文本之间有机地互动。
李利君亦具创作才华,他的小小说涵盖反腐、师生关系、人生哲理等多元题材,紧扣时代脉搏,映照社会现实与人性的复杂纹理。李利君谦称自己是以“指手画脚”之态进入小小说世界的,然而这偶然踏入,却织就了他与此文体一生的缘分。
《热闹》揭示“热闹”的真实含义。在张太那门庭若市的客厅,访客络绎不绝,携来精致礼物与无声的谨慎。一墙之隔,对门却传来阵阵笑声。两种热闹,仅一门之隔,却仿佛两个世界,回荡着截然不同的声音。
小说在“老师,再见!”这一声中轻巧解锁。这不仅是身份的显露,更是两种生活价值与获取“热闹”方式的根本分野。一种热闹源于外在的权威与交换,拥挤、体面而冰冷;另一种则源于内在的学识、尊重与纯粹的共鸣,朴素、真挚而温热。张太在走廊感受到的“萧瑟”,正是心灵失去真实滋养后的空洞回响。
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剥开浮华生活的金粉,让我们直视其下精神土壤的荒芜。小说的力量正源于此:它让每一位身处喧嚣的现代读者,在合上书本之后,不禁侧耳倾听——在自己生活中回荡的,究竟是哪一种热闹?
《阳光与阴影》的故事始于一场沉寂的“回望”——边松远被调查九十九天后,他昔日最得力的助理林若茜,约见了老同事“我”。咖啡馆里,她面容憔悴,言语间浸满追悔,说起那段活在权力光环下的日子,仿佛一场醒不来的梦。如今她已离开,决意将过去清零,开一家奶茶店,一杯一杯,重新把生活泡出味道。
小说以“九十九天”为轴,将一场压抑的忏悔与窗外年轻人的鲜活对谈轻轻并置,宛如过往的沉重与未来的轻盈展开一场无声对话。阳光懒懒铺在桌角,邻桌传来关于落叶纹路的惊叹——那么认真,那么轻易,恍如发现了另一个世界。而林若茜撕开糖包,将整包砂糖缓缓倒入咖啡,不搅拌,任其无声沉落。那一刻的苦涩,早已渗入空气。
语言简短,克制,却字字藏着潜流。“你一点没有感觉吗?”——并非质问,更像一声幽微的叹息。“没有啊没有”——听来轻快,却透出一丝紧绷的回避。叙述者“我”如一面安静的镜子,既映照,又保持距离。故事于是留下大片空白,容读者自行填入未被言明的碎片。它不作审判,只作呈现,犹如一幅用灰调慢慢铺就的心灵素描。
边松远的落马,表面是法律问题,内里却是人在欲望丛林中的迷失。林若茜的转身,则像从一场华丽的梦中醒来,决定赤脚踩回泥土。“鸟兽散”之后,还有“一杯一杯卖奶茶”的笃定。而“我”,或许正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那个沉默的见证者——不落井下石,也不轻言安慰,只是目送,并记得。
《白发》讲述一次再平常不过的茶叙,却让“白发”成为试纸,测出两种人生。退休的曹凤同劝处长张严立染发,“人得有点亮色”。张只是笑笑,任由白发在日光下坦然舒展。一个仍活在宝马香车、茶楼应酬的热闹里;一个甘愿埋首文件,与阳台上的风相伴。后来曹凤同被调查的消息传来,张严立怔了怔,走上阳台——夜色中车河奔流,像无数急于奔赴下一场繁华的梦,而他静静立着,忽然觉得白发不是岁月的落叶,而是时间悄然颁发的徽章。
故事的高明,在于不置一词。那些被省略的“违纪细节”,反而让读者的目光完全落在张严立那片刻的沉默上。“裸喝”与“有内容的喝”,话中含话,却不落痕迹。直到最后才明白,原来真正的亮色,不必染,它在坦然接受时光洗礼的眉目之间。
《老人与玫瑰》像一首藏在时光夹层里的小诗。老人提前一年多来到花店,高价预订一枝玫瑰,只嘱咐一句:“明年九月一日,送到这个地址。”店主明艳依约前往,却发现那是一座墓碑——老人已故的妻子,在照片里对她浅浅笑着,那眉目竟与自己有几分相似。她没有说话,轻轻将“玫瑰皇后”放在碑前,心里却已许诺:每年今日,我都会来。
悬念是一层薄纱,直到最后才温柔揭开。此前所有古怪的细节——闭眼闻香的郑重、一笔一画写下地址的缓慢——在这一刻都有了温度。老人从未说爱,可所有动作都在诉说;明艳也没有多问,可她的泪水与承诺,已让这份爱越过生死,在另一个陌生人的心里,悄悄续写篇章。
《把我埋在柳树底》里的八爷爷,是家族扎在故乡的最后一根老根。临终前,他谁的话也不听,铁了心要埋在荒草萋萋的“柳树底”乱坟岗,绝不进祖坟。秘密后来才揭开——原来年轻时,他曾是大刀会一员,就在柳树底,挥刀斩下鬼子的头颅。不进祖坟,是他死后还要守着那片血浇过的土地。后辈们知晓后,寂静无声,只是默默遵从。小说以家史为线,穿起个人与国运,写得沉静,却字字落在心坎上。
作者不急,慢慢讲。家族如何星散,远行的大伯怎样归来,一本《热河文史》如何成为打开往事的钥匙。真相在翻阅中猛然回转,那一刻,轻飘飘的个人记忆,忽然有了气壮山河的气概。
八爷爷在故事里几乎是个哑巴。他日日沉默,像块旧石头。可正是这石头般的沉默,让最后那句“一刀砍下鬼子头”迸发出惊雷般的力量。原来英雄就藏在最不起眼的粗布衣裳下,藏在一生不肯多言的缄默里。
柳树底,人人避之不及的野坟场,却是他一生的战场与归宿。它像一个被遗忘的伤口,封存着牺牲与血泪。直到八爷爷执意躺进去,这片荒地才骤然挺立,成了一座无字无碑、却人人都能看见的纪念碑。“看死那些鬼魂”——这朴素到近乎粗粝的誓言,让一片土地有了镇守山河的魂。全文语言像从土里长出,情感却深沉如海。
谈及小小说的现代机缘,李利君当年曾说出一段颇具洞见的判断:“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一种为纯文学争气的方式,一种凭借自身智慧赢得利润空间与尊严的方式,一种基于大众审美与纯文学内在关联而科学运作的方式,一种最终以其强大吸引力汇聚数以万计读者的经营方式——就在国内期刊纷纷式微的背景下,走向前台,浮出水面,奏响了刚健、昂扬、前进的旋律。它不降低格调,不出卖立场,只凭扎实的作品与自身的智慧高歌猛进。这就是小小说。”这段话,或可视为一篇“当代小小说宣言”。
作者简介:杨晓敏,豫北获嘉人,当代作家、评论家、小小说文体倡导者,华夏小小说研究院院长。
◆ ◆ ◆ ◆ ◆
附:李利君小小说五篇
热 闹
张太并不太在意对门住的是什么人。她想,总也不会是什么本事大的人。因为,这栋楼东侧是100平方米大小,而自己住的这西侧则是130平方米的。
她的家经常要在夜间接待一些来访者。张太并不是很烦,因为来访者都是毕恭毕敬的,并且都会带一些价值不菲的礼物。没办法,张先生是这个城市的“上层建筑”,住在这套房子里已经算是很廉洁的了。因为门经常开关,她有时会看到对门其实也经常有人来,似乎并不比来她家的人少。不同的是,她家的来访者总是悄无声息地来,又悄无声息地走,可是对门的人却是春风满面地来,又春风满面地走。
这让张太有一点点的意外。
中秋前几天,张太家似乎更忙碌了。人们几乎是排着队进来的,坐上一分钟就离开。张太也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对门的上访量却还和旧日一样。张太劳累的心不知为什么有一点小小的自得。然而,这自得没有两天,就被无情地撕破了。
对门一下子宾客如云,并且,还不时有笑浪传过来。张太心里就有点烦。她其实也希望来自己家的人能带来一些欢笑,而不是什么鱼翅、红包之类的东西。可是,这些人却像前世就修行好了的奴才一样,皮笑肉不笑,搓着手,不知所措的样子。张太脸上早没了什么好颜色,她木然地送上一杯茶水后,就顾自去看电视。张先生经常不在家的。张太知道来访者没话找话其实只有一个目的——让她转告张先生来者是谁。
张太的耳朵里却不时传来对门的欢笑声。她的心早就飞过去了。
送客的时候,张太破天荒第一次把客人送出了门,看那个人诚惶诚恐地下了楼,她有点忍不住地站在门口,想听听对门到底是些什么人这么快乐。声音非常年轻,但不能肯定那是些什么人。这时,楼道里有脚步声,她赶紧进了门。
门铃响了。张太一动不动,看着偌大的客厅,她的心里忽然一阵凄凉。在她听来,门铃声不过是势利的探询而已。她的眼圈有点潮湿。
张先生一步一步奋斗到今天这个位置。前些年,张太跟着他没少受罪,那时他们可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可是,自从张先生突然不用那么辛苦了,她就一下子闲了起来。开始的舒适早已荡然无存,张太觉得自己心里缺少了很多东西。
门铃响过几声之后平静了下来。张太静静地靠在沙发上,对门的声音又传过来。她听着那些声音,记起自己也曾经有过这种快乐的时光。那时他们年轻,无忧无虑,心里充满了对世界的种种美妙的幻想,那时她的内心满是把握这个世界的豪情壮志,当然,在很多人看来,今天,她已经成功了。凡是了解这个城市历史的人都知道,张先生的今天,有一半是她的功劳——其实一直以来,张太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成就也非常满意。可是今天,她突然感到自己失去了一些东西。
她拉开门,看看外面没人,忍不住把耳朵竖起来,仔细地听对门传出来的欢笑声。楼道里有初秋的风穿堂而过,吹在人的身上已经有几分凉意。张太双手用力抱住双肩,缩起身子。外面是无边的灯火。张太想,张先生可能在干什么呢?她想不出。又一阵秋风吹来,我们的主人公张太回转身加了件衣服,又站回到了门口。客厅里和这空旷的走廊一样的凄清。她突然只想站在这里。尽管走廊里的灯是新换的,可是,依然显得有几分暗淡,尤其是不时有笑声从对门飘出来的烘托,张太的身影就显得颇有几分萧瑟。
正当张太像一个贪婪的人沉醉在金子的光芒中的时候,对门的门开了。张太没有准备,她感到一股热乎乎的气流扑面而来,仿佛是春天吹向小草的风一样。她赶紧退回身,脚步在地上滑了一下。她赶紧站稳。就在门将要关上的一瞬间,她听到许多人的声音响起:
老师,再见!
阳光与阴影
“整整九十九天,九十九天了。”坐下来后,我们半天没有说话。咖啡上来后,原总经理助理林若茜转动了一下杯子,这样说。
她是前天预约的我。当时,她的电话打来,我多少有一些情绪上的波动,但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她今天上午十点,来1939咖啡店见个面。老实说,我都觉得这个见面太晚了。
林若茜的变化之大,让我感慨唏嘘。头发没有半点光泽,肌肤已经失去了水分,目光也变得迟缓。过去,她与超凡珠宝集团的绝大部分珠宝一样,靓丽耀眼。
“九十九天,好像一个悬疑故事片的名字。”她笑着说——笑里却塞满了苦涩。
“没事,都已经过去了。”我犹豫了很久,才用这样勉强的话安慰她,连自己都觉得无力。
她说:“我真是没有想到——哈!这口气,是不是太像祥林嫂啊。但真的没有想到。”
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疏疏落落。我看到几个年轻人坐到隔壁。其中一个,从双肩包里拿出笔记本电脑,一边开机,一边恨恨地说:“我特么的都想揍他。这么挑。是不是没喂饱他啊——”
“……别想别的了,别给自己贴太多标签。”我慢慢地说出这几个字。
林若茜说,还用我自己贴啊,浑身上下都贴满了。“我都不敢上网了。”
其实,网络上也没有多少关于她以及边松远太多的内容。只有一条被多家媒体转载的关于边松远接受纪律审查的通稿。有一些媒体开放了留言区。林若茜的名字就出现在评论区里。
九十九天前,边松远是超凡珠宝集团的董事长,林若茜是总经理助理。而我,一直是投资创新部总监。
“你一点没有感觉吗?”她问我,目光里有些幽怨。
“没有啊没有。”我把头扭过去,看那几个年轻人,他们凑到一起,好像在商量解决方案。
边松远被带走当天,林若茜就打了辞职报告——此前的风言风语,由此做实。林若茜没有等任何批复,就离开了公司和人们的视野。我没有太多力气关注她——关于我,说法同样多如牛毛。而我自己很清楚自己。我相信组织,所以,我依然正常上班。我对主持工作的总经理余清润说:“如果觉得我的思路不符合您的风格,调整我吧。”余清润只说了一个字:“哦。”
边松远是超凡珠宝集团的创始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无论工作思路还是执行力,都十分强大。我在想,问题,可能出在股权分配上。当时没在意。
对此,我没有和林若茜多说。我觉得,她应该比我清楚——作为总经理助理,实际上是董事长“一秘”,比总经理掌握的信息量还大。
林若茜对边松远有一种近乎崇拜的感情。他们都是超凡珠宝集团早期的建设者。我是后来集团扩张时,通过应聘进入集团的。我的211学校的学历,还是拿得出手的。
“现在回头一看,都变得好可笑啊——”林若茜说。
“真是不可思议啊。我觉得自己好像中了毒一样——”她用纸巾掩住自己的眼睛。“九十九天,我把这些年的事情都细细地过了几遍,真是,不可思议啊。”
我起身去拿了两包糖过来,她撕开一袋的包装,一下子都倒进杯子。
“不怕甜过头吗?”我给自己的杯子加了一点。
林若茜没有回应我,继续说:“瞬间,一切都如鸟兽散啊。”
“……你不是去过北京吗?”我小心地问她。
“是的!”她的口气里滤去了一切情感,中性地说:“当时,边董觉得不太对,就让我去了趟北京,找了两个人,只说是竞争对手可能在用不规矩的手段。那几个人说会帮助。现在看,几乎是没有意义的表态。”
我不知能说什么了。边松远派出林若茜赴京,他自己应该最清楚自己的事啊。
“也别想了——会有客观的结论的:事实胜于雄辩。”我前言不搭后语。
“嗯。”
有一片树叶,旋转着,斜飘过去,落到了年轻人的电脑上。一个女孩子捡起来,高高举过头顶,对着阳光,惊喜地喊:“这片叶子这么好啊——你们看,它的纹路是这样的,像画的欸!”他们就开始研究叶片了。“年轻真好啊。”我在心里说。大把的时间,可以溜个小号。哪里像我,四十岁一过,只有不敢松懈的奔波。
“我和妈妈如实讲了,妈妈的情绪还好。我也找了纪检组。除了和边松远的关系,我没有其他什么事。”
我不敢接茬儿,静静地听。
“都不知他怎么有那么多时间,还有心思瞎折腾——”林若茜说:“那么聪明的人,那么会做生意的人,唉。”
“谁都有犯糊涂的时候——以后,有什么打算?”我是想转移一下话题。我觉得这真像一场马拉松,气都喘不上来了。“生活还要继续。”
“是的。”她停了一会儿,说:“先休息一段时间——看看给我的结论吧。即使给严重警告,我也不可能回集团了。我想,安定下来,我就卖奶茶去吧……看,就像那样。”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街对面大树下,有个小亭子,一个小姑娘在卖饮料。“一杯一杯地卖,多好啊。”她说。
“是啊——钱,一块一块地挣,踏踏实实。”
几个年轻人叮叮当当收拾东西,椅子推开,说说笑笑走了。
“不耽误你了。你也去继续上班吧——我的信件,麻烦帮我代收一下。其实,不会有其他信件,只是保险公司每个月的通知单。不用拿给我,放你那里就行,或者碎掉——”
她站起来。经过隔壁桌子时,她把几把凌乱的椅子推回到座位下。
马路上的阳光很刺眼。周围大楼幕墙的玻璃反射过来的光,扫淡了路上的阴影。
我眯了眯眼,对林若茜挥了挥手,说:“再见!”
白 发
“你呀!染一下嘛!”曹凤同说,“花不了几个钱。”他啜饮了一杯茶,说,“看着那么凄凉。”
张严立笑了笑:“总是觉得没有时间——”说完了,张严立马上觉得这理由很站不住脚,就补:“不想遮遮掩掩了。年轻时很喜欢美化亮化自己,再有五年就退休了,就这样吧。”
曹凤同:“没有追求,放弃自我管理,就是放弃人生。”
张严立说:“没有吧——我每天要看的材料还是堆成山。毕竟,年纪大了,速度比过去慢了不少。不过,还好吧,一样也没漏。我的人生还在线啊。”
曹凤同:“你这个样子,要是退了休,估计很快就进了大妈大爷的队伍里去——你的人生太干瘪了,没有一点亮色。”
“到那个年纪,就去吧。”
“我才不会呢。我退休至少保证三年继续染头发。喝茶、谈事、应酬……还是挺精彩的。”
“喝茶容易——”
“你理解的喝茶,是裸喝。”
“那还有什么喝法?”
“得有内容。”他笑了,然后,起身下楼、出门。
一辆宝马轻快地停在身边,他拉开门上去。 摇下窗,向张严立挥了挥手,“去染吧,大德路那家。你要是去,给我个电话。染发的钱,我出啊!”
看着那辆车绝尘而去,张严立若有所失,叫了辆的士,回家了。
张严立和曹凤同是老同事——或者说,他是张严立的老上级。张严立进机关时,他当科长。张严立当科长时,他当处长。张严立当处长时,他是厅长——他退了,张严立还是处长。估计以后,也就到这里了。与他在一起,张严立的人生总是处在一个追不上的状态。他开始谈喝茶、谈事、应酬时,张严立还只能改材料。满头的白发,也顾不得理会。其实,也没人太在意。如张严立这般,老处长了,生活也不能说不公平。人在机关,出来总还是有人觉得你不错。张严立就甘于这样了。老婆倒是也满足得很:“这样挺好的。”张严立看着她每日忙着买菜做饭、上班下班,一个普通的妇人。也许她也曾有过荣华富贵的梦想,可是,张严立没有带给她。她也认了。
回到家,她知道张严立和曹凤同刚才在一起,略有一点不悦:“你少和人家掺和。老是跟在厅长屁股后面,你不觉得别扭吗?”
“那么多年的老同事了,别扭啥?”张严立打开电脑,进入微信,调出明天开会要用的材料,开始了大修。
“啥同事啊。人家是厅长,你是处长。知道不?”她打开吸尘器,嗡嗡嗡地推着在房间里转。“咱们呀,不贪图那个,但也不用去凑他的热闹。你自己觉得是同事,人家可不一定那么想。可何况,别的人看了,还以为你拍马屁呢。”她的声音被吸尘器的声音盖住了。
张立严并没有听清她咕哝个啥。他对着电脑屏幕看了一眼自己:“要不要染呢?”他自问。古人云“白首搔更短”。张严立的头发倒是没短,还是那么密密实实的。只是——白。“白了少年头”——那是无病呻吟,如今,张严立白的是“中年头”,也就没有什么悲伤的了。
张严立没有去染头发。中间曹凤同几次给他电话,约着吃饭——张严立担心再提染头发的事,就借故推辞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某一天,张严力突然在清风网上看到一则短讯:曹凤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审查。
张严立一下子就懵了:怎么会这样?
这个时候也不宜给任何人打电话。晚上,张严立没有改材料,只是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马路上的车流。真像一条河啊,哗哗啦啦地流向夜色深处。张严立想起了很多往事,一幕一幕,生动却又模糊。在张严立成长——或者说工作的路上,基本上就是一个木讷的人。曹凤同就笑过张严立“笨”,不会利用资源。张严立其实也不知道如何利用资源,或者用资源来干什么。他说过,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你没有朋友。”的确,除了有数的几个人,张严立真的没有热热闹闹、前呼后拥的朋友。对这座城市,除了上班的机关大楼、附近的几个公园和菜市场、医院,就不怎么熟悉别的地方。不像曹凤同,熟知咖啡厅、茶楼、大酒楼和小资的一些“吧”。作为师弟,张严立的确和他相去甚远。张严立的同学来了,也都是找他,由他来约张严立。原因当然是因为张严立不咋地的实际情况。
晚风吹过来,张严立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从阳台的位置向外,张严立每天都会望一眼,城市似乎没有尽头地向远方延伸而去。几座标志性的建筑张严力也很清楚。可是,他依然觉得那些深深浅浅的灯火是陌生的。
生活或许本就如此吧。
风吹过,他的头发耷拉下来几根。快三个星期没理头发了,有点长。他用手往上梳了一下。这时,张严立突然想到,曹凤同今后应该也会本色生活了,头发也不会染了。其实,张严立一直不知道他白发会是什么样子。他会剪短发吗?
至于张严立的白发,就那么个样子吧。
那是岁月的馈赠,不可强求,也不可强求。
老人与玫瑰
老人蹒跚着,走进花店。刚刚失恋的明艳压住了自己最近的失落,从屏风后面走出来:“爷爷,您买花?”明艳想,会不会是路过看花,或者是要买一束菊花?这里靠近小区,经常有人进来看看花。也因为在小区边上,也有老人来买花,去看刚刚离世的老朋友。
老人停了一会儿,慢慢转过头,看了明艳一下,点点头,颤颤巍巍地说:“我要买一枝玫瑰!咳咳!”老人用手挡住嘴巴。明艳心里想:老人买玫瑰,不多啊!她抽出一支递给老人:“都是今天早晨进来的。你看,多漂亮多香啊!”
老人咳完了,笑盈盈地看着明艳:“我看得到玫瑰的漂亮,但香不香,得闻一下啊!”
明艳想,这是个较真儿而且调皮的爷爷呢!她的心情得到了调节一样积极起来:“对对对。您闻一下,香得不得了!”
老人闭上了眼睛,凑近鲜艳的玫瑰,闻了一会儿,缓缓地说:“真香啊!”
“给奶奶买回去,奶奶一定会年轻十岁的!”明艳开心地说。爷爷买玫瑰,不送给奶奶,那能送给谁!明艳理直气壮。
“哦哦!”老人没有多说什么,认真地查看着花瓣。
“放心吧,爷爷,朵朵娇柔!”明艳认为老人在检查玫瑰的质量。
“嗯。”老人转头看着明艳。
明艳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爷爷,我说的都是真话!”
老人说:“我信你了——你的眼睛这么坦诚,不会骗我。”
明艳被他这么一说,又有点不好意思了,害羞地低下了头:“爷爷,您一定很爱很爱奶奶的!”
老人竟然红了脸,还有些小小的慌乱:“也没有……”
明艳笑了:“您都脸红了,好像刚刚谈恋爱呢!”
老人闭了闭眼睛,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姑娘,这玫瑰多少钱一支?”
“爷爷,您这么爱奶奶,我给您打五五折:30块。”这是真的。要过情人节了,玫瑰贵到飞起来。
老人把手慢慢伸进斜背着的挎包里,再拿出来时,已经抓了一沓钱了:“这是3000……”
明艳被震惊了:“您要一百支啊?”
“不!只要一支!”
“那只要30就够啦,爷爷!”明艳以为老人听错了,就大声说。
“没错,我就要一支,也要给你3000……”老人说。
“爷爷,这,这,把我造蒙圈了!”明艳摸着后脑勺说。“我要是收了您这钱,只给您一枝玫瑰花,那不是天理不容吗?”
“姑娘,我不是现在要!”
“那您什么时候要?”
“明年9月1日——公历啊。”
明艳更糊涂了:“爷爷,您是不是记错了。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呢。”
“没错,没错——”老人又咳起来,“不好意思,姑娘,人老了,唉,真是啊!不争气,不争气,这身体啊,不是自己的,自己做不了主啊……”老人语无伦次地絮叨起来。
“哎呀!爷爷,您别急,慢慢说。如果是明年的话,您明年再来,现在太早了。明年,我给您留玫瑰皇后!”明艳安慰老人。她想,这真是一个有故事的老人!
“唉!姑娘,你不懂,也不用劝我。我现在预订,给你这些钱,是让你到时候给我送到一个地方——”老人着急地说。
明艳糊涂得不得了,但她还是说:“爷爷,你把地址给我,我一定给您送到。但钱不用这么多!”
“你不收这么多,我不放心!”老人说:“你要是不收,我还得去别家——人人都说过你这里服务特别好的。”
这倒是真的,明艳诚信为本,街坊们赞誉有加。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明艳想,先收下来,到时再退给他就好了。“好吧,爷爷。你把地址写给我。我到时让人送过去——”
“你一定要亲自去——别人,我信不过!”
明艳想,哦,原来是这样的原因出的高价啊。明艳不知道为什么要让自己去,但也不多想了:“爷爷,地址写下来给我。”她把笔和记事本递给老人。
老人一笔一画地写下了一个地址。明艳看了一下,不熟。反正是明年送,到时导航一下就到了。
“姑娘,你读一遍,我听听你是不是记准了。”
明艳笑着说:“爷爷好细心啊!”她读了一遍,老人听完了,点点头:“对的,就是这个地方。拜托,一定送到啊!”
“爷爷,我送到了,一定给您报告!”明艳立定、敬礼,俏皮地说。“哦!收花人姓名呢?”这才想起来,显得就不那么专业了。明艳自己都笑了。
“张竹笋。送到了,你不用报什么告了,我信得过你。再说,你也找不到我……”
老人交代完毕,离开了。
明艳看着他转弯,蹒跚的背影消失了。心里虽然有点淡淡的好奇,但马上就消失了。她发现,自己的心情变得轻松起来。发生了什么?好像什么也没有。她顾不得多想,忙着迎接新来的顾客。此后,明艳倒是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了这事。“有故事。”她想。
日子如流水,似乎一下子就到了第二年的9月1日。早晨,明艳让新来的雇员看住店子,自己开着电动车,按照导航,到老人留的地址那里送花。
车子七拐八拐,进入一个大花园,然后穿过一个花径。前面是台阶了。她停下电动车,捧着花,拾级而上。等到了地点,明艳发现,这是一个私人墓地。她吃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苍翠中,一座半人高的白色墓碑。
明艳按住狂跳的心,抬头看看天空,高远纯净。再环顾四周,安安静静,没有一点危险的样子。她慢慢走上前,发现白色的碑上有一张小小的照片。她长出了一口气,慢慢凑上去,她更惊讶地发现,那女人竟和自己有几分像。墓碑上几个字:张竹笋女士之墓。下面括号是:“1940.9.1——2000.9.1”。
生卒纪念日竟然都是今天!
明艳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又突然觉得明白了什么。她向四周看了看,仿佛周遭有好多眼睛在注视着她。
莫名地,她的泪水瞬间充满了眼眶。然后,顺着脸颊流下来。她用袖子抹了一下眼睛,上前半步,轻轻地,轻轻地把那支玫瑰放在墓碑前,深深地鞠了个躬:
“爷爷,您放心吧。以后每年的今天,我都给奶奶——”
停了一下,她纠正了自己,继续说:“给张竹笋女士——不!”泪水汹涌而下。她断断续续地说:“给奶奶,带来,一、支、玫、瑰、皇、后……”
把我埋在柳树底
爷爷兄弟八人,他行三。伪满洲国时期,按照类似于“不能把鸡蛋装在同一个篮子里”的理论,兄弟八人分为两拨,爷爷和六爷爷、七爷爷、八爷爷留在老家,大爷爷带着另外三位爷爷到了三百里外的林东。说好了,哪边的日子过好了,另一边的就过去。可是,他们永无合二为一的机会了——几个爷爷都慢慢顶门立户分家过日子,两处的老李家都成了当地的大户人家,再动一下就难了。大爷爷去世后,就在当地下葬了。此后,到了林东的那一支李氏有人去世,就葬在当地。
老家这边,六爷爷分出去另过;七爷爷和八爷爷都是老光棍,终身未娶,一直和爷爷在一起。爷爷就我父亲一个儿子,家里的人也并没有显得太多。爷爷去世前,交代父亲照顾好七爷爷和八爷爷。父亲奉行“百善孝为先”的准则,做得不错。七爷爷去世后,我们也渐渐长大了,对八爷爷也是完全与亲爷爷一样。
八爷爷是个和善的老人。我记得爷爷在世的时候,他总是跟在爷爷的身边。他们老哥仨喝酒,八爷爷温酒、倒酒。大家一起干活儿的时候,八爷爷总是那个打下手的角色。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话少得可怜,好像一辈子的话都已经说完了似的。
八爷爷吃完饭,放下碗,把我父亲喊住:“有话跟你说。”
父亲坐在沙发上,但八爷爷半天没有说话。他们俩抽了一通烟后,父亲看了一眼八爷爷:“八叔!”
“这样,我这日子怕是不多了。有件事,得交代给你。”
“啊?”父亲把嘴里的烟拿下来,“八叔,你觉得不舒服吗?”
“不是。年纪大了,总归要走的。我怕哪天死得顺利,来不及交代。”
“你看你,你急啥呀!”父亲笑了,说。
“还是早点儿说了吧,省得到时你们省了力,我闭不上眼……”
“怎么了,八叔?”父亲紧张起来了,生怕自己哪里照顾不周,或者家里谁惹了八爷爷不高兴。
“没怎么,就是……我死后……不要埋在祖坟里。”
“不埋在祖坟里,那埋在哪儿啊?”父亲大惊道,“八叔,您老这是怎么了?”
“没怎么。”八爷爷淡淡地说,“你给我记住:把我埋在柳树底。要不,我饶不了你!”说完,他就出去了,扛起一把锄头,去了后山。
柳树底是离村子一里地左右的一个河沟沟,过去是有人家的,但是出入很不方便,那里的人就都搬出来了。小时候,我们一不听话,大人们就说:“再不听话,就把你扔到柳树底喂狼!”听说柳树底是一个乱坟岗子。八爷爷放着祖坟不进,要去乱坟岗子?难道他还整过啥见不得人的事儿,不敢进祖坟?但这样一想,我们都觉得太扯了——八爷爷那么厚道、老实。那么,到底是咋回事儿?父亲百思不得其解,我们更是蒙查查。
八爷爷这样交代了,如果不照做,那不也是不孝?但,要是把他埋到柳树底,村子里的人不是要把我们的脊梁骨戳烂?
父亲又和八爷爷聊了一次,但八爷爷没有多说什么,就一句话:“把我埋在柳树底!”
父亲很是为难。
“这个……八叔啊八叔!这不是为难我吗?”有时候,父亲和我们嘀咕。
后来,母亲提醒他:“找个德高望重的人来劝一下。不进祖坟怎么行啊?要是一个混蛋,杀人放火男盗女娼的,想进还不能让他进呢。”母亲说,八爷爷是世上难找的好人。她举例说,那年闹地震,半夜里房子晃荡,八爷爷冲进里屋,一把抓起我和弟弟冲出去了。“那次,全仗着你八爷爷了,要不,你们几个……”听得我们一愣一愣的。
找谁呢?这个也不是容易的事。
八爷爷已经是全村年纪最大的了。
这时,母亲灵光一闪,想起来了:“林东的大哥!”
感谢改革开放,这些年日子好起来,我们和林东的李氏家族重新联系上了。母亲说的大哥,指的是大爷爷的大儿子。他仅比八爷爷小三岁,和八爷爷说得上话。去年打电话时,他身子还很硬朗。
我们觉得是个好主意。父亲就打通了电话,问候了之后,父亲跟大伯讲了八爷爷的心愿,问他:“大哥,你说这可咋整?”
“啊!这你都不清楚啊?”没想到大伯这样问,反倒把父亲弄得更蒙了。
“这样吧,我过几天回来一趟,看看老八叔,也顺便给你们说说。”
过了几天,大伯和我的几位年纪不轻的堂兄从林东开了个车队过来。父亲自是高兴,把其他堂兄弟喊过来,一起来见最年长的大哥,一时好不热闹。
父亲把镇子上最大的饭店大厅包了下来,李氏家族的老老幼幼全部到场。八爷爷高兴得嘴都咧到了耳朵根子,耳朵和眼睛都忙不过来了,听大伯给他介绍:“这是我二叔那支的,这是我四叔那支的,这是我五叔那支的……”
所有人落座后,父亲清了清嗓,请大伯讲几句。
大伯把椅子向后推了推,要站起来的意思,父亲小声说:“大哥,您就坐着说吧!”
“不行!”大伯站起来,说,“咱们这一大家子,现在又聚会,这可以算得上百年盛会了。很多老一辈的人已经看不到这个盛况了。可是,咱们还有八叔,八叔看到了。他高兴。今天呢,我还想宣布一个事。这个事,是当年我爹告诉我的,交代我不能说,但是,今天,我想当一回逆子,我还得说啊!”
我们都觉得十分诧异,不知道大伯要说什么。
“老根子,不能说!”八爷爷颤巍巍地要站起来制止大伯。
“八叔,这事,是咱们家的光荣。咱们老李家,以后不能出孬种,得告诉他们!”大伯让八爷爷坐下,然后,他从随身带着的一个小提兜儿里拿出一本书:《热河文史》。他翻开,然后,把书举起来:“这里说的,就是你们的八爷爷,我的八叔!”
父亲把书接过来,看了一眼,大声地读出来:“李凤英一刀砍下鬼子头……”
原来,八爷爷十几岁时,就参加了大刀会,随大刀会的人一起杀鬼子。一次,鬼子“扫荡”,经过柳树底,进了大刀会的伏击圈,双方发生了一场激战。战斗中,八爷爷砍掉了一个鬼子的头!
父亲读完全文,大厅里爆发出如雷鸣一样的掌声。
大伯等掌声小下去,说:“孩子们,你们要记住,国难虽然是一时的,但,英雄啥时候都不能没有。没有英雄,就没有家,没有国!”
…
过了几天,大伯返回林东。临走前,他和八爷爷相拥,泪水长流。
“八叔,你放心吧!到时候,我盯着这些兄弟,一定让你睡在柳树底,替我们看死那些鬼魂,让他们永无翻身之日!”
李利君创作随笔:
我们对小小说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深化的,它作为文学队伍中的一员的审美特征以及小小说的种类等,都会随着小小说实践而不断变化和丰富起来。现在,我更愿意我更认同一个观点:小小说是瞬间的艺术。
如果用大量概括手法行文,那就未必是小小说。它应该与长中短篇小说有着一样的文学光芒、审美特质。由此,我提炼出一种小小说新美学特质,即:“极端瞬间”。
由于种种原因,我选择了要在2000字内即小小说的方式完成我的文学冲动。为了这2000字,我会把我看过的资料从厚达几公尺读到薄薄的一页纸,然后,选择矛盾即将到达顶点的那个瞬间。比如,一个领导干部在风声起的时候开始作为起点,然后,会安排一个陪衬性的人物,展开叙述……这样,在极端瞬间内完成人物命运的转换,留下一些感慨唏嘘。
由于“极端瞬间”要压缩时空,砸实矛盾冲突,所以,产量一般不会很大一一极端瞬间毕竟是能量的爆发,而不是细水长流,需要足够的精力和阅历。
作者简介:李利君,广东作家,出版小说集《等到天亮》、评论集《小小说的九十年代后》、散文集《湛江:中国的飘带》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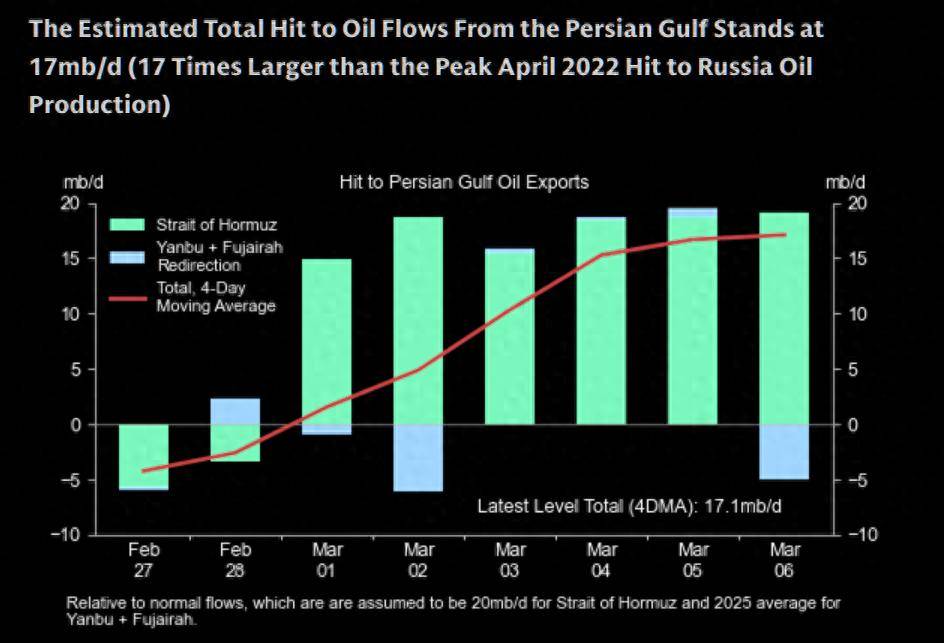






- 最新
- 最热
只看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