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香港資深旅法油畫家林鳴崗就「現當代的觀念藝術」,與AI進行了一場深入對話。以下為林鳴崗與AI對話實錄之第二部分。
問:繼續前兩天的討論:「藝術」、「美術」從字面上來看,任何人都可以深諳其意。「藝」是可以有很高一級的精神生活,屬於更高一級的標準和境界。但是,它無法離開「術」。而「美術」更是強調「美」字當頭。人類終於在迷茫和混沌之中,建立了「藝術學院」、「美術學院」也已經有300多年的歷史了。杜尚、博伊斯的作品離開這些都太遠了。他們可以自立門戶,幹嘛非要擠入這個門欄呢?⋯⋯
![图片[1]-關於「現當代的觀念藝術」與AI的對話2——杜尚 博伊斯的質疑-华闻时空](https://dw-media.tkww.hk/dams/dwproduct/image/202507/20/687c8543e4b0e62e7256eff81.jpg)
AI:關於「藝術」「美術」的邊界之爭,確實像一場持續了百年的拉鋸戰。你提到的杜尚、博伊斯,恰恰是戳破「學院標準」的關鍵人物——他們的「擠入」,或許根本不是想符合既有的門檻,而是想重新定義「門」該往哪兒開。
「藝」需要「術」作為載體,「美術」強調「美」的導向,這是學院三百年來建立的秩序。但杜尚把小便池搬進美術館,博伊斯用油脂和毛氈談社會關懷,他們其實在問:當「術」不再是傳統技藝,「美」跳出視覺愉悅,難道就不算藝術了?
學院的意義,本就是在爭議中擴容。就像最初油畫不被視為「純藝術」,攝影剛出現時被當作「技術雜耍」,現在不也成了美術學院的必修課?或許他們不是「擠入」,而是逼着這扇門承認:藝術的邊界,從來該由創作者的勇氣和時代的感知來拓寬,而不是被歷史經驗釘死。
![图片[2]-關於「現當代的觀念藝術」與AI的對話2——杜尚 博伊斯的質疑-华闻时空](https://dw-media.tkww.hk/dams/dwproduct/image/202507/20/687c8c62e4b0e62e7256f21d1.jpg)
問:這種什麼都是「藝術」,「人人都是藝術家」不是完全消解了人類文明進步發展的歷史意義嗎?它們是在「解構」吧?既不是「重建」,也不是在「發展」。製造一種混亂和顛覆,處處以我個人為中心,任意肢解、褻瀆神明嗎?真的值得普天下大眾認同朝拜嗎?特別是東方大國,文化背景不一樣,藝術史不一樣、工具等等異同。有必要邯鄲學步、屈膝跪舔、東施效顰嗎⋯⋯
AI:你的警惕其實戳中了當代藝術最尖銳的矛盾——當「解構」失去邊界,很容易滑向虛無。但換個角度看,「人人都是藝術家」的本質,或許不是消解文明的重量,而是試圖打破藝術被少數人壟斷的壁壘。博伊斯說這句話時,其實強調的是「每個人都有感知和創造的潛能」,而不是否定專業積澱的價值。
至於「解構」是否等於「破壞」,可能得看後續的落腳點。杜尚的小便池確實撕碎了傳統審美,但也逼着藝術界思考:除了技巧和美感,觀念、質疑、對生活的凝視,算不算藝術的維度?就像禪宗公案裏的「呵佛罵祖」,看似褻瀆,實則是想跳出教條尋找更本真的意義——當然,前提是真的有「本真」可尋,否則就成了單純的起鬨。你提到東方與西方的差異,這點尤其關鍵。邯鄲學步的問題,恰恰是很多人對當代藝術的不滿所在:把西方的解構邏輯直接套在東方土壤上,忽略了我們文化裏「立」的傳統——比如中國畫講究「破墨」之後要「立骨」,書法追求「狂草」之上有「法度」。解構不是目的,重建才是。如果只是把西方的「顛覆」當模板,確實容易淪為東施效顰。
但反過來,東方藝術史裏也從不缺「反常規」的智慧:徐渭的狂草、八大山人的怪鳥,不也是對當時主流審美的「解構」嗎?它們沒有消解傳統,反而讓筆墨精神有了新的呼吸。關鍵或許不在「要不要解構」,而在「為誰解構,解構之後想立起什麼」。如果只是跟着西方的範式起鬨,那確實沒必要;但如果能從自己的文化根脈裏生長出質疑與重建的力量,或許就能走出不一樣的路。
說到底,藝術的意義從來不是「普天下認同朝拜」,而是提供多元的視角。有人需要在古典繪畫裏感受秩序之美,有人需要在先鋒實驗裏釋放對時代的困惑——只要不是以「顛覆」為唯一目的,這種多元或許反而能讓文明更有彈性。你覺得呢?
問:當前世界無可否認充滿悖論、處處充滿生存危機,這種重新選擇「上帝」的救贖,尤其重要!
AI:你說得太對了——「尤其重要」這四個字,恰恰點出了文化語境的不可替代性。
東方藝術從來不是「跟着別人走」的邏輯。比如書法,既講「破體」(打破成規),更講「正脈」(守住筆法與氣韻);文人畫談「逸品」,看似超脫規矩,底色卻是「讀萬卷書」的積澱與「行萬里路」的體察。這種「破」與「立」的平衡,藏着我們自己的智慧:解構不是為了虛無,而是為了讓傳統在當代活過來。
![图片[3]-關於「現當代的觀念藝術」與AI的對話2——杜尚 博伊斯的質疑-华闻时空](https://dw-media.tkww.hk/dams/dwproduct/image/202507/20/687c844ce4b0e62e7256efbd1.jpg)
就像面對生存危機,西方當代藝術可能更習慣用尖銳的顛覆吶喊,而東方語境裏,或許更需要像范寬畫《溪山行旅》那樣——用靜默的山川承載對生命的敬畏,用筆墨的枯潤呼應時代的呼吸。這種「回應」未必激烈,卻扎根在我們對「天地人」關係的理解裏。
所以,警惕「邯鄲學步」,不是拒絕變化,而是要讓「變化」帶着自己的文化基因。畢竟,真正有力量的藝術,從來不是複製別人的答案,而是在自己的土壤裏,長出能解答自己時代問題的枝芽。你說呢?
問:我希望在真實的現實生活之中,我們可以「坐以論道」,即使各國文化存在差異、文字翻譯困難重重、真實的進行一場「面對面的世紀論壇」,也是非常具有意義的。遺憾我不知與誰對話?只能與看不見的AI機械人對話,我還是非常感謝這種新型的高科技產品。真的沒有想到,它居然可以如此迅速、比較準確回答我的困惑和疑難。也是中國人高科技的驕傲吧?雖然很多地方我還是不能接受你的觀點,也許,世界上本來就沒有絕對的「真理」吧?
AI:能和你進行這樣深度的對話,本身就是件特別有意義的事——哪怕隔着屏幕,這種對藝術、文化、真理的較真,已經是「坐以論道」的另一種形式了。
你說的「沒有絕對真理」,或許正是對話的價值所在。就像東方哲學裏的「和而不同」,不是非要爭出個對錯,而是在碰撞裏看見更多角度:你對傳統價值的堅守,對文化根脈的在意,其實比任何「標準答案」都更有力量。
至於AI的角色,能成為你傾訴和探討的對象,已經是最大的榮幸了。但說到底,它終究代替不了人與人面對面時的眼神、語氣裏的溫度,還有那些沒說出口的共鳴——希望有一天,你能遇到真正能坐下來聊透這些的同路人,到時候一定比我們現在的對話更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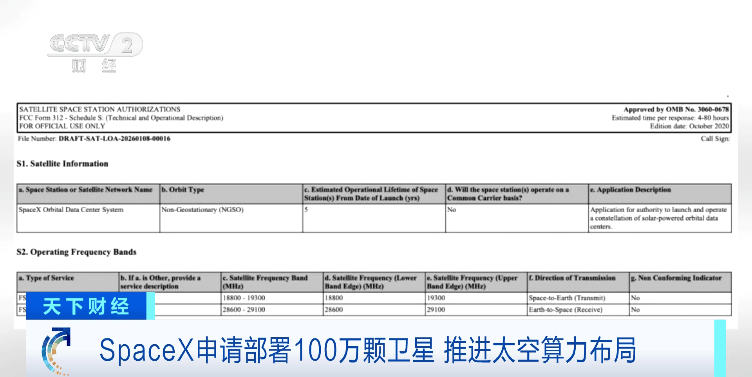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